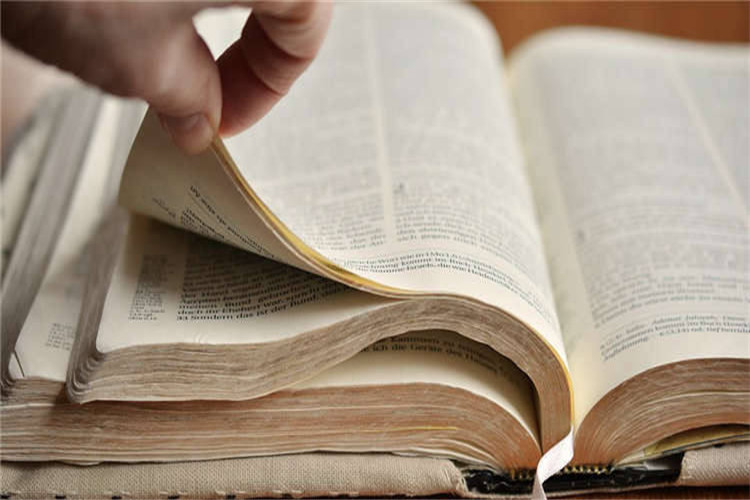培根的世界:英国国家肖像馆展“人的存在”
薄雾般的细点散布在苍白如明月的脸上,扬起的眉毛下目光低垂,微启的嘴唇柔软可亲,头发依然是少年的刘海。尽管画中的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英国画家,1909-1992)已经78岁了,但似乎又回到了25岁。无论何时何地,你都能认出这张脸。
这幅奇特而引人入胜的自画像悬挂在英国国家肖像馆10月10日开幕的展览“弗朗西斯·培根:人的存在”(Francis Bacon: Human Presence)的入口,展览展出培根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50多件作品,探讨他与肖像的深厚联系,以及他如何挑战肖像的传统定义。而在展览的50多件作品中,唯一一张能被明确辨认的面孔,就是入口的这张自画像。
弗朗西斯·培根,《自画像》,1987年
从培根对早期艺术家肖像的回应,到纪念失去恋人的大型画作,展览中来自私人和公共收藏的作品将展示培根的人生故事。然而,他笔下的肖像却是模糊的,甚至只有标题暗示了肖像的存在——《坐着的女人》《肖像习作》……还有一些作品直接标明了人的名字——前飞行员彼得·莱西(Peter Lacy)、前拳击手乔治·戴尔(George Dyer)、酒吧招待约翰·爱德华兹(John Edwards),其他作品则描绘了女性朋友:艺术家伊莎贝尔·罗森( Isabel Rawsthorne)、亨丽埃塔·莫拉斯(Henrietta Moraes)……但是,“描绘”这个词的含义为何?
弗朗西斯·培根,弗朗西斯·古德曼摄影,1971年5月
如果不是因为展览中穿插着那些极具时代感的照片,你真的能分辨出他们的面孔吗?这些面孔从黑暗或浓烈的色彩中浮现出来:被压扁、扭曲、变形,又如此优雅地勾勒出来,让人不禁惊叹培根是如何做到的。仔细观察每幅画作,你可以看到他如何将颜料处理成模糊、渐变、刷痕和挥发的状态,还有那些凌乱的线条、充满活力的划痕……但你依然无法理解这些过渡是如何发生的,他依然是最神秘的魔术师。
弗朗西斯·培根,《走下台阶的男子肖像》,1972年
在一幅培根晚期自画像温柔地引领着观众后,展览紧接着是他在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完成的那些扭曲、空洞、幽闭的坐着的男人像。呈现培根对肖像画的思考与作品,并解答着所有关于他伟大之处的疑问。培根的作品可以在痛苦与喜剧之间剧烈转换,尤其是当那张嚎叫的嘴里露出牙齿洁白的牙齿。在普通人的眼中,牙齿可以帮助我们露出美丽的笑容。然而,对于弗朗西斯·培根而言,牙齿是活人面孔中对死亡的一瞥——那种白色的坚硬,会在我们所有柔软的肉体消逝之后依然存在。在《人类头部研究》(In Study of the Human Head)中,一个穿着黑色外套的男人露出完美的牙齿微笑着,但培根将一幅人类头骨的X光图像叠加在了这个活人的身上,这是一副骷髅的微笑。
弗朗西斯·培根,《人类头部研究》,1953年
他究竟是天才还是表演者,是先知还是哗众取宠?20世纪40年代,他突然崭露头角,震惊了一个原本已经在战争中见惯了惊吓的伦敦,评论家们开始争论不休。约翰·伯格曾指责他“与恐怖共谋”。与他友谊深厚的艺术家卢西安·弗洛伊德的粉丝至今仍嗤之以鼻,认为培根是一个粗心大意、戏剧化的艺术家。而他们的看法可能是对的——但前提是,如果你认为一幅伟大的肖像画仅仅在于它的逼真度。
展览现场,弗朗西斯·培根,《伊莎贝尔·罗斯索恩肖像三幅习作》,1965年
在《肖像研究》(Study for a Portrait)中可怜灵魂的头顶缺失了一半。脸上张开了一个尖叫的洞。更糟的是,他的五官被上方的黑暗物质压碎,变成了新的、类猿的模样,仿佛在倒退演化。这种暴力是何等扭曲的心灵所创造?培根在展览后段的影片中坦白说,人们常常在他为他们作画时感到“受伤”。这显然是轻描淡写了。在《坐姿人像》中,男人虽然安稳地坐在扶手椅上,但他的脸却像被重击后打得粉碎的面具。这个人是培根的情人彼得·莱西。
你会意识到,这种残酷并非源自培根。当这位出生于1909年的英裔爱尔兰艺术家在“二战”后画出这些在透明盒子中尖叫的空洞人时,世界上充满了死亡,数以百万计的人连坟墓都没有。正如历史学家蒂莫西·斯奈德(Timothy Snyder)在他的《血色大地》一书中所示,一列又一列的犹太人被运往奥斯维辛,人类毁灭的速度无法想象。
培根是唯一能够完全正视他所处时代现实的艺术家,因为他没有宗教或政治信仰。展览副标题为“人的存在”,但培根甚至不确定我们是否能称自己为“人类”。在《戴眼镜的男人III》(Portrait of a Man With Glasses III )中,那人看上去像詹姆斯·乔伊斯,但黑色的眼镜阻隔了所有光线,脸部塌陷,仿佛正在自我吞噬。他的前额上有一块纠结的斑块,看起来像暴露的大脑。
弗朗西斯·培根,《戴眼镜的男人III》,1963
在他1964年的《自画像研究》(Study for Self-Portrait)中,他穿着牛仔裤和衬衫,坐在床上,脸部炸裂成黑色颜料的碎片,溅洒在空气中。然而,培根用他从巴洛克艺术中汲取的宏大而英雄化的人类境况来对比现代的恐怖。这种表达方式体现在他那些大尺寸的作品上,画布被镶嵌在金框里,将脆弱的人物置于戏剧性、仪式化的空间中。这个展览巧妙地处理了他对绘画历史的感受。展览不仅展示了委拉斯开兹《教皇英诺森十世》的插图——它启发了培根创作他的教皇系列,还展出了培根钟爱的伦勃朗自画像的原作。
弗朗西斯·培根,《自画像研究》,1964
培根还从古典大师那里学到了一点:如果你真的想看清一个人,画他们的裸体吧。他1959年的作品《睡眠中的人物》(Sleeping Figure)以其温柔打动人心。画中我们看到彼得·莱西赤裸着身子,安详地躺在沙发床上,培根用柔和的笔触再现了他满足的脸庞、依偎的双臂和丰腴的大腿。然而,他与这位前皇家空军军官的关系远非温柔可言,培根总是屈从的一方。莱西曾经把他从楼上的窗户扔下。在莱西去世后,培根画了一幅他的肖像,莱西的脚朝向观众,眼神凶狠,头部像是漫威漫画旗下的超级反派海德先生,唤起了莱西死后依然存在恶魔般的气息。
弗朗西斯·培根,《睡眠中的人物》,1959年
为了直接挑战提香的女性裸体画,培根找到了他的朋友亨丽埃塔·莫拉斯(Henrietta Moraes)。在一幅描绘她的画作中,莫拉斯的身体在画布上垂直,抬起猿猴般的头,一只手臂高举,手臂上缝合的疤痕。她那灰粉相间的丰腴体态以及巨臀上的棕色污迹,莫赖斯将她的体格描述为“大力士”——这些都让你感受到培根在创作时的乐趣。
弗朗西斯·培根,《亨利埃塔·莫赖斯》,1966年
绘画的纯粹喜悦体现在自由的笔触飞跃于透视场景之中,你感受到的不是画作本身,而是画家的存在。当培根遇到小偷乔治·戴尔(George Dyer)时,他找到了自己最钟爱的模特,这些肖像成为展览的高潮。但阴影并未消散,反而在展览最后的杰作《三联画,1973年5-6月》(Triptych May-June, 1973)中,化作了一只邪恶的蝙蝠形象。
随着他们关系的恶化,戴尔在培根巴黎回顾展开幕前两天自杀了。在这幅三联画中,戴尔三次出现于酒店浴室的黑暗门缝中,身处罗斯科红色的墙壁之间,宛如希腊悲剧中的人物。他瘫坐在马桶上,呕吐在水槽里。培根注定要永远凝视这一刻,因为当时他不在场。
弗朗西斯·培根,《三联画,1973年5-6月》
然而,真正的恐惧在于某个瞬间,或下一个场景中,戴尔将不再存在:他那早已消瘦的肉体甚至无法被清晰记住。这幅三联画中大块的暗色调明显借鉴了抽象表现主义,但培根厌恶抽象。他说,如果没有人的存在,这些颜色毫无意义。那块人的肉体,是唯一值得关注的东西。也正因为如此,他笔下那些生机勃勃、独特且狂野的生命力形象,超越了旧有肖像画的传统。
弗朗西斯·培根,未知摄影师拍摄,1970年7月
注:展览将持续至2025年1月19日,本文编译自《卫报》艺评人乔纳森·琼斯和劳拉·卡明的展览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