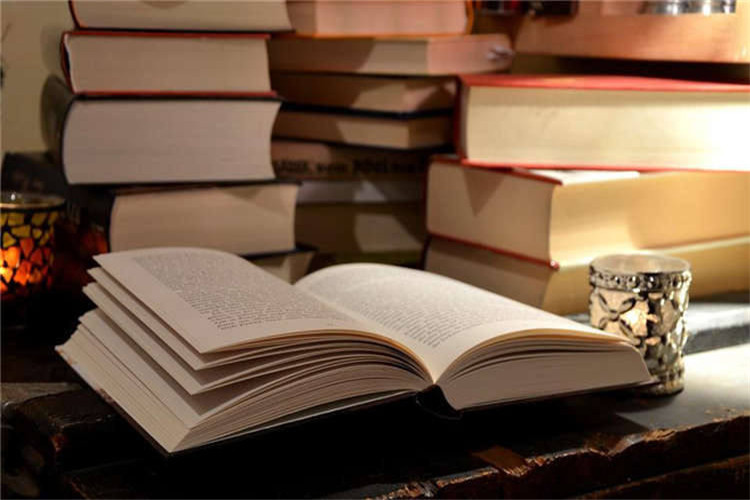尼采诞辰180周年|作为音乐家的尼采
如果没有音乐,生活将是一个错误。
——弗里德里希·尼采
上世纪80年代,著名尼采研究学者、作家周国平策划编写了《诗人哲学家》一书,一时洛阳纸贵。周国平力邀当时国内思想界的诸位名家,为国人介绍了12位富有诗人气质的西方哲学家的生平、思想以及他们对人生的思考——包括帕斯卡尔、诺瓦利斯、施莱格尔、克尔凯戈尔、叔本华、尼采、狄尔泰、瓦雷里、海德格尔、萨特、加缪、马尔库塞。在那个思潮即时尚的年代,人们怀着如饥似渴的情状陶醉于各种新的思想、理论和观念。尤其是弗里德里希·尼采,伴随着他的“上帝已死”的惊世骇俗的名言,成为那个时代最激动人心的名字之一。曾几何时,一场关于尼采的讲座能涌进几万名听众,其空前绝后的盛况不亚于如今一场顶流歌手的现场演唱会。事实上,尼采不仅是一位具有诗人气质的哲学家,更是一位有着浓厚音乐情结乃至音乐家气质的哲人。可以说,对音乐和作曲的热爱贯穿了尼采的一生,也成为打开尼采思想世界大门的一把金钥匙。
演奏钢琴的尼采
缪斯的召唤
1844年10月15日,尼采出生于莱比锡附近的一个新教牧师家庭,许多音乐大师如J.S.巴赫、亨德尔、舒曼、瓦格纳等都在这座音乐名城生活过。由于父亲是路德教派的牧师和教师,尼采自幼浸淫在宗教音乐中。虽然童年先后经历了父亲和弟弟的离世,但母亲开启了他早于智性启蒙的音乐教育——尼采6岁开始学习钢琴,并通过自学掌握了作曲技能。1854年5月25日,尼采聆听了亨德尔的神曲《弥赛亚》,这是一次洪荒初始的心灵风暴,不能无一,不可有二。当《哈利路亚》的歌词响彻整个教堂时,尼采体验到的不只是宗教上的慑人力量,更是音乐艺术的巨大震撼。后来,尼采回忆起这段往事时,历历如昨:
听到这《哈利路亚》庄严的合唱,一股冲动,让我差一点也张口附和;但欲唱又止,因为这是属于天国之音。当下,立志决定,也非要谱出这般的曲子不可。离开教堂后我马上狂奔回家,极喜地坐到钢琴前,尽兴地尝试着各种不同的和弦,每一个和弦的音响、色彩,皆让我久久不能自已。
在此,音乐的种子在尼采身上诞生萌芽,虽无声无息,却惊天动地。就在这一年,经受音乐艺术洗礼的尼采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创作才情,写下了自己的第一首作品——《为钢琴而作的稍快板》(Allegretto For Piano),他自信十足地在谱面中间签上了自己名字首字母的缩写“F.N.”(Friedrich Nietzsche)。
14岁时,尼采迎来了音乐创作道路上的第二个转折点——进入普福塔中学(Schulpforta)。
与一般学校不同,这所中学重视的不只有拉丁文和希腊文,还有缪斯的语言——音乐。尼采在校期间加入合唱团,并且浸淫在所谓的“希腊古典精神”中。不断感受到的强烈而深刻的音乐体验,加上自幼厚积薄发的音乐教育,让尼采感受到一种背离于西方基督教禁欲色彩的召唤。由诉诸感官的音乐艺术所带来的内心悸动,与基督教根深蒂固反官能式的精神洗礼,在尼采的内心产生了狂风骤雨般的冲突。在越来越逼仄的航道内,尼采需要找寻一个生命的出口,一种新的“生命美学”,借由熟稔希腊古典文化之便,他找到了一个最佳代言人——酒神狄奥尼索斯。由此,《悲剧的诞生》之前奏已然鸣响。
对音乐和诗歌的双重兴趣,让尼采天然地与古希腊精神的气质高度吻合。古希腊时代的歌手,手持一小竖琴,自弹自唱,集诗人与音乐家于一身,他们除了能美声歌赋之外,亦能即兴创作填词,为文学与音乐的缪斯之子。六年普福塔中学的青少年岁月,尼采以其在文学领域上的广泛涉猎与浓厚的人文艺术熏陶,使其音乐作品转型为艺术歌曲的形态,集诗歌与音乐于一身,这正是他对古希腊精神的一种身体力行的实践。在这所文艺氛围浓郁的学苑中,尼采撷取了德国历代浪漫派诗人的杰作,谱曲入乐,化为一首首艺术歌曲。
由于身处浪漫主义暴风雨的中心地带,尼采在音乐风格上受到浪漫主义运动的影响最为深远。一大批德奥作曲家如J.S.巴赫、海顿、贝多芬、舒伯特、门德尔松、舒曼等都是他所钟情的大师,他也喜爱肖邦,因为他从小就认定自己有波兰贵族血统。尼采最早的一首歌曲《门前一隅》写于1861年,词取自德国诗人克劳斯·格罗斯(Klaus Groth)的同名诗作。这首歌描写了一旅人少小离家老大回后的感叹:“外面纵使再耀眼诱人,但世界上最美的地方仍是家中庭院前之一隅”。在这首初试啼声的作品中,可由音乐色彩的轨迹上看出,尼采明显浸染于典型舒伯特式质朴无虑的音乐语言世界。
对于音乐和诗歌的关系,以及背后所蕴含的酒神精神,尼采在70年代中后期写作的《人性的,太人性的》一书中说道:“音乐不仅是一最能直接表达内心情感的语言,在上古时代,它还与诗歌结合,与声律的节奏、语调的强弱息息相关。如此一来,它真正具备了能直接与我们的内心‘对谈’的特质,一种语言的特质,并且是一个发自内心深处的语言。”在尼采看来,“发自内心深处的语言”仅有一种,即“仿效音乐声响”的那种,那是酒神的语言。在此,尼采为酒神与音乐的直接关系做了感应式的映照,而这些独特的哲思与感悟的源头,正可以追溯到他在普福塔中学求学期间的音乐体验与创作。
尼采与瓦格纳
1864年,20岁的尼采进入波恩大学修读神学和古典学,前者是家人的要求,后者才是自己的兴趣所在。让他对基督教信仰产生动摇的诱因,正是一次次深刻的音乐体验。在波恩求学期间,尼采频繁地观看各种歌剧和音乐会演出,他的音乐创作兴趣主要集中于将裴多菲和普希金的诗歌谱写成艺术歌曲。次年,尼采转学莱比锡,他的命运再次迎来了一个重大事件——他在莱比锡的一家旧书店读到了叔本华被人遗忘的杰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叔本华哲学带给尼采的那种深深的沉醉与震撼,丝毫不亚于亨德尔的《弥赛亚》。
《瓦格纳事件:尼采反瓦格纳》
无独有偶,生于莱比锡的歌剧天才理查德·瓦格纳同样是叔本华的绝对拥趸。不难想象,当尼采与瓦格纳在1868年的莱比锡结识时,两人那种一见如故之感是如此强烈,以至于迅速产生了一种深深的友谊之情。对尼采而言,强烈吸引他的,不仅是瓦格纳在音乐上的成就,还有对方对叔本华哲学理念的认同——他们多次热烈地讨论《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经由共同的精神导师,尼采与瓦格纳的相遇成为现代思想史上的一个关键事件。我们可以从尼采日记中的一段文字,来了解一个年轻心灵的震撼:
与瓦格纳相处的这段时间,可谓是有生以来,最情感洋溢、令人动容的日子,只能说:他是当代无与伦比的天才与人杰。每隔二、三周,我总会成为他们位于琉森湖畔旁别墅的座上客,几天下来的相处,让我得以就近亲领他的风采,这,可说是我生命中最丰收的体验,而这一切,需感谢叔本华。
1870年代初,两人的友谊达到巅峰。瓦格纳将《论贝多芬》的文稿寄给尼采,后者则投桃报李地回赠以《狄奥尼索斯的世界观》,这正是日后的名作《悲剧的诞生》的草稿。怀揣着对瓦格纳的崇敬和对音乐艺术的热情,尼采在音乐创作上开始脱离往昔的古典小品,转向编制较大、气势磅礴的风格。这一时期,尼采创作了题为《除夕夜之终曲》(Nachklang einer Sylvesternacht)的钢琴曲,这首作品展现了鲜明的瓦格纳印记:除了曲式上的仿效之外,尼采使用了瓦格纳歌剧中常见的“主导动机”,以及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1865)里特有的和弦色彩。
对于这首创作于两人友谊高峰期的作品,尼采格外珍爱,并称之为“狄奥尼索斯的告白”。在《悲剧的诞生》一书里,尼采清楚地阐释:“在希腊阿波罗式的规矩范畴里,呈现了另一种狄奥尼索斯生命意志力的表象,此两种截然不同的意志对峙,实际上,是有一种非凡意义存在的,即创造一个更升华的可能性,同时,经由艺术,来抵达一个更耀眼的歌咏赞扬。”在此,我们看到了这一时期尼采在哲学写作与音乐创作的道路上,平行采用了狄奥尼索斯的诠释,他所期许的酒神精神,不只让思想跃然纸上,亦能纵情于音符之间。无疑,这是一种崭新的生命美学观点。
《悲剧的诞生》
然而,两人的关系在1874年呈现出急转直下的态势。尼采越来越多地看到自己与瓦格纳的不和谐,他在笔记中描述瓦格纳“具有双重性格,难以相处,傲慢自大;他的主要特点之一是缺乏节制与适度;他把一切都做到极致极限、穷其力量,滥用其情感……”。1876年10月,瓦格纳和尼采在意大利小镇索伦托重逢,他们迎来了一生中最伤怀的时刻。最后一晚,两人在小山上散步,已是晚秋,“颇有些永别的意味。”瓦格纳这样形容。当时,瓦格纳讲起了他正在创作的《帕西法尔》(1882)——他一生中的最后一部歌剧,让尼采吃惊的是瓦格纳谈论的是一段个人的宗教经验,而尼采一直认为瓦格纳是个无神论者。分别之后,混杂着悲伤与失望,尼采在笔记里写道:“当我发现他原来竟是这样一种人时,他的成就在我眼里顿时失去了所有价值。”
其实,尼采与瓦格纳的疏离除了人性上的冲突之外,更重要的是两人在艺术理念和生命美学上的差异。在尼采看来,“谁如果想要克服颓废,就必须要经历颓废”,只有在这种生命力的虚弱之中,才会产生一种更高的艺术的灵感。后来,尼采撰文批判瓦格纳,并结集成作品《瓦格纳事件》(1888)一书,将瓦格纳视为欧洲近代文化疾病的表征。不过,与瓦格纳的那段友谊始终珍藏在尼采的内心。瓦格纳去世后不久,尼采得了严重的精神疾病,他在文集《快乐的科学》(1882)中留下了一段关于友谊的自白:
我们曾经是朋友,现在陌生了……我们恰恰因此而变得更加彼此敬畏,对当时友谊的想念恰恰因此而变得更加神圣……我们愿意相信我们星辰般的友谊,即使我们相互不得不成为陆地上的敌人。
据说,在发病前的几个星期,尼采热衷于在钢琴上即兴演奏,而弹奏的大部分都是瓦格纳作品的旋律。
音乐与欧洲文化
世人皆知狂人尼采的哲学思想,却不知他对音乐的狂热。终其一生,尼采始终是一名音乐的狂热爱好者,并始终将音乐视为最有哲学深度的艺术。在《瓦格纳事件》中,疯狂前的尼采不停地发问:“可曾有人注意过么,音乐能解放人的灵魂?音乐能给思想插上翅膀?一个人越是一个音乐家,就越是一个哲学家?灰暗的抽象的天空被闪电所照亮,那光亮如此之强,使得一切细节都无处遁藏,人因而能发现问题,因而能从山顶鸟瞰世界……”从早期的《悲剧的诞生》到晚年的《权力意志》,尼采的思想始终与音乐艺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尼采的终极理想是复兴欧洲文化,哲学与音乐则是他的两大路线。
回顾尼采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传统与革新的激烈碰撞无处不在。在音乐领域,两条截然不同的艺术之路越来越明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一方面,许多人推崇由巴赫、海顿、莫扎特、贝多芬开拓的古典主义传统,继而由舒曼以及后来的勃拉姆斯得以传承;另一方面,以柏辽兹、李斯特与瓦格纳为代表的“未来音乐”派,以其对音乐艺术的大胆革新为自身迎来了时代的青睐,成就了一条众人拥戴的光辉坦途。最终,形成了勃拉姆斯与瓦格纳这一对守旧与革新的音乐宿敌,以及相应的两大音乐阵营。而在尼采身上,不难看出其更加倾向于坚守古典主义传统的影子。
在那个现代艺术的颓废时代,尼采直言“我和瓦格纳一样皆为时代的孩子,即我是一名颓废者。惟一的区别是我正视这个事实,并与它抗争,而他则不是。”于是,尼采在《瓦格纳事件》激烈地批判了后者:“我的心灵已经告别了瓦格纳。⋯⋯因为他回到了德国,他逐渐认可了我所轻视的每一样东西。很明显,在瓦格纳最高成就的时候,他已经成为了一个腐败的、令人失望的颓废者并且被立刻摧毁,他孤独而破碎地出现在基督的十字架面前。”在尼采看来,瓦格纳已经几乎等同于基督教的颓废。他的问题是,过分的演出技巧,自我宣泄癖,放弃了真理,把音乐和悲剧变成了一种安慰的手段。
与此同时,尼采在比才的音乐中找到了音乐艺术的理想化身,它似乎体现了反对瓦格纳音乐的所有特点:那些音乐“是丰富的,简洁的。它构筑、组成,它完成了。它是音乐息肉的对立面。没有任何愁苦的面容,没有任何伪造品!《卡门》省去了宏大风格的欺骗性。”在此,尼采再一次从古希腊精神中找寻价值,在长久地陶醉于狄奥尼索斯精神之后,他需要为欧洲艺术尤其是音乐艺术恢复阿波罗精神。“我们一定要把地中海风气带进音乐当中,去思索比才并且取消瓦格纳笼罩在我们头上的雾气⋯⋯回到自然,回到健康,回到欢乐,回到年轻!”于是,面对着走向颓废的欧洲文化,尼采喊出了那句著名的话语:“我要看一点窗子了。空气!更多的空气!”
笔者收藏的《尼采艺术歌曲与钢琴作品集》
在尼采看来,“构成人的真正形而上活动的是艺术,而不是道德。⋯⋯世界的存在只有作为审美现象才是合理的”。这种泛审美主义使传统的审美领域扩大到审丑领域:情感的疆域挺进已失去任何边界,创造成为了新艺术的唯一目标。就这样,尼采的强力意志和超人哲学为现代主义艺术和后现代主义艺术奠定了思想基础。所谓“超人”就是这样一种不断破坏旧传统、不断创立新艺术的生命强大的天才。现代主义的艺术家们高举尼采的榜样,进行不断破坏和创新的实验,走向艺术的“先锋”。在音乐领域,印象主义音乐、表现主义音乐、形式主义音乐不断登场。西方音乐经过近500年发展所形成的理性、感性之间的协调和平衡,在以勋伯格为代表的新维也纳音乐中开始解体。
勋伯格从无调性的情感表现主义走向了十二音体系的形式主义道路,与斯特拉文斯基的形式主义音乐殊途同归,共同体现了现代主义音乐艺术高度重视音乐自身的形式美以及不断创新的基本品质,这正是尼采泛审美主义思想所蕴含的不断超越的终极奥义。作为音乐家的尼采,没有留下一部世人所熟知的音乐作品,但音乐对其伟大哲学思想的影响却无处不在,让不断走向衰落的欧洲文化在日暮西山处留下了一片绝美的夕阳余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