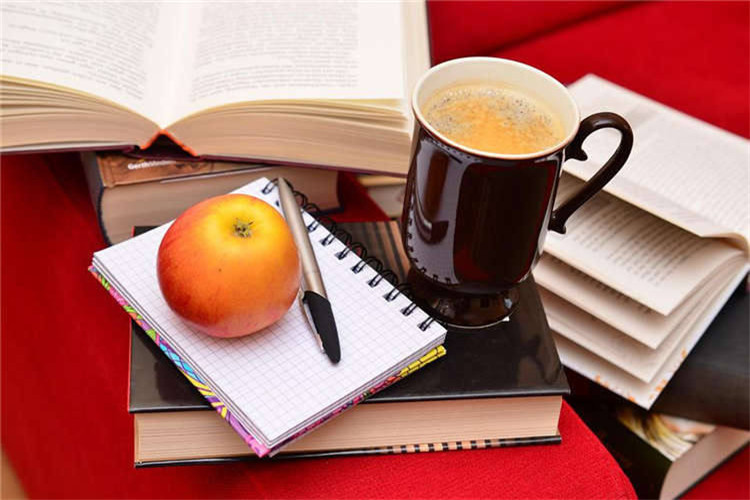界面新闻记者 |
界面新闻编辑 | 黄月 尹清露
说这禅寺是闹市中的一方净土,不为过。即使最繁盛的旅游时节,这里仍可取静……卧听竹林叶响,冬夏皆可观游鱼……因是桧木打造,天气静朗时,能隐隐地闻见极清凛的气息……
这是作家葛亮笔下的志莲净苑,位于香港市区中心的宝刹之一。现如今,这番古典雅致的园林意象似乎已因当代文化的众声喧哗而渐趋游离于时代,但葛亮认为,闹中取静,沉淀与悦纳,恰是当代人应有的思考面向。这也是他在其新作《灵隐》中的观念。
继“家国三部曲”(《朱雀》《北鸢》《燕食记》)之后,《灵隐》开启了他新的写作系列“南方图志”。小说分为“父篇”、“女篇”、“番外”三个章节。性格温厚的南华大学教授连粤名,因犯下伦常血案被捕,围绕他的一生,牵连出粤港百年历史变迁。女儿连思睿兼负罪犯家属、变性者恋人、智障孩子的单亲母亲多重身份,蒙受各路舆论冲击。告别学生时代后,连思睿于尘世与佛堂之间安顿心灵,重启人生。粤港大地上的百态众生,其遭际与应对,亦各成历史又彼此交叠。
葛亮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博集天卷 2024-8
葛亮日前接受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专访,探讨了他对时下的省思、对个体的关照,及其书写下的“当代人的心灵史”。
01 嘈杂时代消泯共情与自我决定的机会
界面文化:你酝酿《灵隐》用了五年时间,可否介绍一下成书过程?
葛亮:《灵隐》脱胎于2018年中国香港地区的一起社会案件:一位大学教授因为种种原因杀害了他的妻子。这在香港地区乃至香港以外一时甚嚣尘上。我一方面作为小说创作者关注到那个案件;另一方面,主人公的身份让我产生了行业共情。我们一直称大学是一个相对封闭的、高尚的人文空间,何至于让教授做出这样一个有悖人伦的行为?
任何一个社会案件或重要的社会现象,最初期引起的反响往往都介于大众层面,这种甚嚣尘上对某些深层次的东西势必有所遮蔽。我不想以相对轻率的、众生喧哗甚至狂欢式的着眼点去呈现这位知识分子,而是希望穿透表层,探讨其行为背后整个的心灵动线。另外,任何个人行为都是在ta所生长的时间路径之下产生的选择,我也更加关注源自时代的因由,一些更深层次的元素。这需要有相应的沉淀。
从18年跟踪这个案件到当下,小说的创作周期伴随着我作为小说创作者本身的沉淀过程。在某种意义上,这个案件为“南方图志”系列的开启给予了一个契机,为从个人的角度切入时代、切入历史提供了很好的入口。
但是入口的进入需要一个过程。书的封面上引用了元代高僧惟则的诗句“人道我居城市里,我疑身在万山中”,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当下人的处境:我们身处的时代太过嘈杂,信息频密的甚至高压的传输已经对我们造成压迫,使我们失去了应有的共情感,也消泯了我们自我决定的机会,不得不屈从于网络时代单向的信息传导。这也成为我写这本书的另一缘由。
界面文化:《灵隐》浓缩了当代人的苦难。例如父亲连粤名身为南华大学教授,学界党派林立,妻子精神分裂;女儿连思睿的恋人在变性手术后丧生,自己也因父亲杀妻案而蒙受疾风骤雨般的网络暴力。
遭逢性别认同、舆论冲击这些似乎独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课题,连家父女的态度却始终是温煦而平和的,读者仿佛看见赛博空间里婆娑着旧日的灵魂。你是否有意营造一种时代的错置感?书中人物所面对的命题是当代的还是永恒的?
葛亮:你所说的“赛博空间里婆娑着旧日的灵魂”,很对应于我在后记中写到的志莲净苑。它位于香港闹市,是亚洲现存最大的全木构仿唐建筑,身居其中,仿佛回到了古典静谧的园林。一抬头,四周却都是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这势必有种非常强烈的错置感,甚至是倒置感,一方面是古典沉静,另一方面现代、仓促和压迫感又时刻扑面而来。我们作为当代的书写者,一定会面对这一系列压迫性的命题。
这时个体需要做出某种选择。直接的抗衡是一种方法,这种应对最终会走向另一种极端。而闹中取静,沉淀之后的柔性判断,更接近于我们当代人的思考面向。
所以,小说中存在着一个引渡者的角色——段河。他是一个青年人,原本是澳门赌场里的发牌师,后来成为了造像师。按照收留他的庆阿爹的说法,造像过程中的放水、去柴、等待,是在去除他的“业”,因荷官这份工作充满了生活的爆裂感。此后他成了别人面对社会问题的引渡者,特别是连思睿。连思睿在拯救恋人林昭的过程中留下了一个孩子,成为了单亲母亲,同时父亲连粤名身陷囹圄,使她成为罪犯的女儿。这些扑面而来的压力,都是现代社会的象征和隐喻,此时出现了引渡者段河。段河引渡的意义除去连接了传统和现代,亦承载了连思睿作为一个现代人所面对的生命镜像,给予了她一个园林。她可以安定下来,有所栖居——这就是心底一片可停驻可灵隐的园林的意义。
界面文化:你多次提到园林的意象,古典园林对你的写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葛亮:园林在美学角度对我影响非常大。包括童寯、阮仪三、陈从周在内的几位大家,其生命观、美学观体现于他们的造园方式。在我看来,建造园林的美学理念可以和文学加以融通。
陈从周先生有一篇文章叫《说园》,提出了看园的两种方式。一种是“动观”,即跟着景色走。他以拙政园为例,从戴月迎风起跟着园林整个的动线在走。另外一种叫做“静观”,即驻足而观。前者是“径缘池转,廊引人随”;驻足而观则需要停下来,通过不同的角度去看园林,这时“看”的动作是由我们作为主动的观照者发出的。面对当下纷繁的社会现象、社会事件的冲击,我们是需要驻足,停下来,甚而是慢下来的。
对于创作者,长篇小说的写作也类似一项建造工程。我曾经写过一篇《梓人的观看》,梓人对应于现代的建筑师。我自比梓人,认为小说的结构也是一种文学的观看方式,作者通过结构的编排,把看到的世界表达给读者。
02 历史充满了演进和诉说,而不是铁板一块
界面文化:不同于此前的“家国三部曲”包罗时代兴衰,《灵隐》愈加聚焦当下,更侧重个体应对苦难的心灵史。这是否是你书写微观历史的一个新的尝试?
葛亮:“家国三部曲”的确将大叙事——特别是晚清以降辐射至今的线性历史——作为写作的主脉,但也已经含有我自身对于历史呈现方式的某些反思。例如《北鸢》中的石玉璞(原型是褚玉璞,在上世纪20年代担任直隶省长兼军务督办,鼎盛期与张学良、张宗昌并称奉鲁直三英)算是一个纵横捭阖式的人物。当政敌刘珍年威胁到其政治地位的时候,他的夫人说了一句话:“你造出了时势,就莫怪时势造出了他这个英雄。”写这句话时我就在想:我们总是陷入对历史和个人之间二元思考范式的拘囿,这是否是唯一谛视历史的方式?
葛亮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01
我们还是要把个人嵌入到历史中去考量。我写褚玉璞,并非写他在沙场上的纵横捭阖、时代风云变幻间的指挥方遒,更多关注他在家庭里做为丈夫、长辈、父亲的状态,希望还原历史人物为“人”,还原宏大情感为人之常情。所谓“风起于青蘋之末”,除了“大风起兮”的大叙事,我也开始注意“青蘋之末”的意义——它其实指向一个又一个的个人。
个人应对茫茫时代的心灵史,含有非常深重的个体烙印。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仍然是把“万骨”嵌入“一将功成”的大叙事图景,但我们可以把个人本身作为历史演进的方式进行谱写。每个人都可以是孤独的历史,有自我编年的方式,既不是屈从于所谓的“大历史”,也不是与“大历史”博弈或是反拨它,而是遵循自身的生长之径。
在此情况下,我开始写《灵隐》。我特地分成了几个章节,从父亲的角度、女儿的角度各自缔造个体的历史。同时它们又相互打通,父亲生命中有女儿的故事,女儿生命中有父亲的命运。甚至看似自成一体的关于女性乌托邦的番外,也嵌入到了连思睿的个人史,形成了互文关系。它像一个又一个器皿,每个人甘苦自知的同时,也可以通过交流沟通,让彼此映照存在。而这种体验最后扭结成了完整的微观史的群落,不再是铁板一块、不容置疑的“大历史”。它可以是多元的、丰富的,同时充满了演进、诉说、体验中的博弈抗衡,产生更多开放性和不确定性。这些恰恰是我想在新的作品系列中表达的。
界面文化:关于聚焦个体生命历程反倒扩充了历史书写的开放性和不确定性,你可以具体说说吗?
葛亮:历史的开放性和个人史之间是相关的。在《灵隐》中很难看到明确的事件逻辑的走向,它一直是围着人物走。既然是罪案,多数人会处理为事件逻辑甚至于推理逻辑,但我最后选择的是尽量涤清我们对于案件的刻板印象,还是进入到人本身。所以中间有一系列的留白,结尾也是开放性的。
这也反映了我近期历史书写的倾向。写《北鸢》时对我近百岁的祖辈有过直接的访谈,老人家谈到一些具体的事件,他今天和明天说的很有可能是不一样的,他的记忆在不同场景下有颠倒重复甚至自我推翻。这对我很有冲击:我该怎么去把握真实?后来突然有一刹那我猛醒了:为什么要用我的史观来拘囿一位老人表达历史的方式?也许他是对的——历史就是博大的、开放的、不停被推翻又重生的。
这对我的史观的冲击非常大,也造就了《北鸢》以及后来的《燕食记》中历史的演绎方式,由此也为《灵隐》做了铺垫。虽然《灵隐》的体量没有“家国三部曲”庞大,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我目前为止史观最为集中的表达。它脱胎于一个社会案件,但远远大于对案件本身的谛观。
葛亮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2-8
《灵隐》的英文书名Hidden Spirit也和个人历史相关。通常,历史的演绎方式是要被说出来的,然而中国的表达方式和西方是有区别的。西方人更重视宣之于口,好比纳博科夫的作品Speak Memory,强调把记忆讲出来,但是中国的艺术和文学中有更多言未尽而意达的部分。
中国人有一些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通俗表达,比如“孩子还小”、“大过年的”、“人都走了”,它提供的不是具体信息,而是营造了一个语境,在此语境之下我们达成心灵的交汇和共识,这和西方特别是美国的低语境文化大相迳庭。文学也是如此。“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镜湖三百里,菡萏发荷花”,都是以景造境,话不多,胜过千言万语。“灵隐”在某种意义上是文化中沉淀下去的部分,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部分,是我们中国人缔造心灵的方式。
回归到此前的问题,为什么连粤名教授面对如此之多的变故和苦难,却可以一种相对舒展淡和的方式去应对?这或许就源自于中国人长期沉淀所带来的对时事的包容感。对历史的缔造也是一样。虽然《灵隐》书写当下的社会,存在一些相对锐利的部分,但我希望用我们自己的心灵去稀释和沉淀它们。不仅展现我们的生活观、世界观,甚而还有美学观。
界面文化:即便是个人的心灵史,也不仅指代事件或经验,还包含如何言说以及为何如此说,就像舞台上的同一幕剧,不同的打光方式创造了迥异的“真实”。你偏爱的打光方式是什么呢?
葛亮:“打光方式”的提法非常触动我,这是更高层面的美学的认证和谛视。电影采取的镜头语言与这个问题非常相关。
不同于文字留给读者自行演绎的开放空间,影视作品天然含有霸权,因为所摄形象直观地存在于那里。但我特别喜欢的一位日本导演小津安二郎选取的处理方式是,他所有的作品都采用一种“枕头机位(pillow shot)”,特别是拍人的特写时,有微微的仰角。这除了代表他的美学观、生命观,也代表了他对于真实的理解:镜头所摄之下,塑造了形象的同时,给予每个人物以同等的尊重。
对个体的尊重也是我想在《灵隐》中传达的。书中有些人的选择非常锐利,无论是庆师傅毅然选择了出家,还是林昭决定做变性手术,以及连粤名精神失常的妻子袁美珍和原生家庭的断绝。但在我表达他们的个体选择时,希望不假臧否,而是以自己的理解将其呈现出来。此时,对于世界乃至个体的一种微微仰角的态度,给了我很大启发。我作为作者也需要将自己的价值判断“灵隐”,在我们这种高语境文化的共识下,相信我与读者之间可以达到对于历史缔造的默契。
界面文化:你会以饮食作为其中一种承载历史和记忆的要素,曾说“食观即史观”。《灵隐》中也有大量有关饮食的书写。在你看来,食物怎样塑造了我们的文化记忆和生命经验?
葛亮:首先,食物表达了人类的记忆,从“大历史”到个人史,构成了非常重要的文化载体。同时,食物也是打通感官的具象化的表征。
从记忆的角度来说,在《燕食记》里,向太史(原型是晚清京官、美食家江孔殷,一生嗜好美食佳酿、古玩收藏)和他的侄子向锡允有过一段对话。他说:“当年我和兄长,同师从追随康南海,同年中举,同具名公车上书,但命运殊异。我和他吃的最后一餐饭,只一道菜,就是这菊花鲈鱼羹。只一壶酒,是他从晋中带来的汾酒。”这时历史是什么?就是一壶酒和一道菜。食物是非常有力的历史表征,其对记忆和文化观念的塑造可以超越语言、习惯、倾向、立场。吃饭的一桌人不知道彼此的来处,但味蕾共同被打通的瞬间却可以凝聚为群体。连粤名和袁美珍为什么会走到一起?有一句广东话叫“撑台脚”(一对情侣吃饭,一起把桌台撑起来)。这就是一种生命共识,因为桌上几道菜,他们达成了休戚与共的关系。
食物作为史观的意象关联着我们刚才讲到的“静观”。香港的茶楼杏花楼,原本是一个饮食空间,却实现了对于历史的定义。很多历史大事件都在那里发生。1895年,孙中山、杨衢云、《德臣西报》的记者黎德等人就是在这茶楼包间里草拟了广州进攻方略和对外宣言,确定成立共和政府后选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史书中的历史往往呈现为非常规整、谨严的面目,然而却是三教九流鱼龙混杂的茶楼这样的社会边缘空间,帮助躲避众多眼线而缔造了“大历史”。这是多么吊诡的事实。
食物也代表了时间的刻度。《灵隐》中写到了几个年节。例如开篇的观音诞,庵堂之内,绕佛的过程中,阿嬷带着女眷们一起准备下锅煮百人的斋菜,盛大的仪式最后还是落实于饮食。食物定义了中国人的节庆概念,端午吃粽子、中秋吃月饼,这就是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食物也浸润了人物自身的生命体验。从个人生命史的刻度到“大历史”的刻度,就是由这有情有味的一粥一饭定义的。
03 无需减少内耗,苦难也是生命历程的一部分
界面文化:书中你反复提到“香港也有座灵隐寺”,江南与岭南之间因而构成了某种文化对位。这是否意味着你认为两地文化间存在某种共性?
葛亮:我之所以强调这句话,是想表明我们对某些概念和空间有成见和刻板印象。比如一提到“灵隐寺”,就是杭州的灵隐寺(建于公元326年,所谓有“仙灵所隐”),这座寺院可以称为“古刹”。但是,原来香港也可以有一座灵隐寺。这座灵隐寺于1928年由臻微法师在羌山山麓建造,又经过灵溪法师的“力肩修托,致力晨禅”,香火也近百年了,但是远远称不上“古刹”。
“原来香港也有一座灵隐寺”,“也”这个字意味着,首先,我们需要去除某种刻板印象;其二,在新的空间中也有一种新的解读的可能。这就涉及到你讲的文化对位。我们身处自己的个体空间或一己之见时,对于另外的可能性是排他的。而当我们真正意义上体认到平行空间中的多样可能性,将开启全新的世界。当你知道香港也有座灵隐寺,和你脑海中的古典的古刹产生了某种对应关系,你会释放各种想象力,去看世界、人生、历史。
在《灵隐》的第二部分,当每一个小节都出现了这句话的时候,引出的是一段又一段的关于人本身的自我体验。这提供了一个契机:我们的生命是可以被打开的。
另外,所谓的中国叙述也长期叠合于中原叙述,印刻在“中国文化”中的“安土重迁”、“落叶归根”,都是北方的概念。即便南方也不是铁板一块,在江南、闽南、岭南的历史和地理的多元气象中是存在对位的。当我讲“香港也有做灵隐寺”,是在刻意和所谓的古刹引出的有关历史的想象拉开距离——我要讲另外一座灵隐寺的故事,是和岭南有关的,多元的,瑰丽的。我们可以站在香港的灵隐寺北望那座古刹,同时,围绕香港灵隐寺发生的南方故事,也在和北方的历史叙事产生反哺和对话。
界面文化:早先几年还有评论说,葛亮笔下的人物是有佛性的。《灵隐》更是“一半佛陀一半神”,一切惊心动魄都于佛性智慧中归于平和。联想到近期年轻人自愿入寺修行成为一种时尚,你认为宗教或民间信仰在当代人的心灵境遇中承担了怎样的角色?
葛亮:我听到时下很流行的一句话,“当代青年人在上学和上班之间选择了上香”。但总结为宗教的意象又过于绝对,反而是每个人需要在当下的生活,特别是升学、就业等庞大的压力之下去寻求心灵的栖居。
佛教中所谓苦集灭道,将现实中的三千烦恼“一念无名”;我们也总想逃脱现实,去往诗和远方,但这反而会加固处理具体问题时传统和现实中间的壁垒。实际上,引渡的意义恰恰在于学会认可生命中的相遇和承载。
我打过一个比方:所有人像是在一列火车上,只能看到半边的风景。也许它让你欢呼雀跃、沉浸其中,让你认同,引以为生命的全部,但你一直没有意识到,你忽略了另外一边的风景。《灵隐》的意义恰恰在于,在充满了车马之喧的现实中,去善待生命中的一切所遇。
我们总是强调要和苦难和解,我觉得不然,苦难也是和生命历程共生的一部分。我们不需要求得减少内耗,让生命一马平川,每一枚生命碎片凝聚在一起,才构成完整的人。
界面文化:同样富有张力的还有小说中的人名,譬如年轻的引渡者换做“段河”,不幸的孩子偏偏起名“阿咒”。这样的命名暗含了怎样的应对遭遇的方式?
葛亮:这首先仍然是对刻板印象的去除。命名通常代表着我们的希冀乃至祝福。比方说有人名叫“艳丽”,就会自我感觉美丽;名叫“明亮”,就仿佛生命充满了色彩。这种自我暗示或归属也会形成某种局囿:人会被标签化。
在这本小说里,我会反其道而行之。给一个年轻人起名叫段河(断河),置于死地而后生,让一个不受祝福的孩子就叫“阿咒”,凸显出生命的张力。
小说中有直接关于命名的讨论。当连思睿受到来自外界的强大压力,段河问她:“这么多年你的名字如影随形,已经对你构成了一种诅咒,你为什么没改名?”连思睿说:“改了名字,能改命吗?”
因此,姓名是重要的又是不重要的。它虽然标签化了我们,却没有必要通过更改名字实现表面的回避。面临诅咒时就叫“阿咒”,他人以为无可皈依时就叫“段河”。当我们认可、承载和接纳它的时候,名字做为标签的意义随之而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