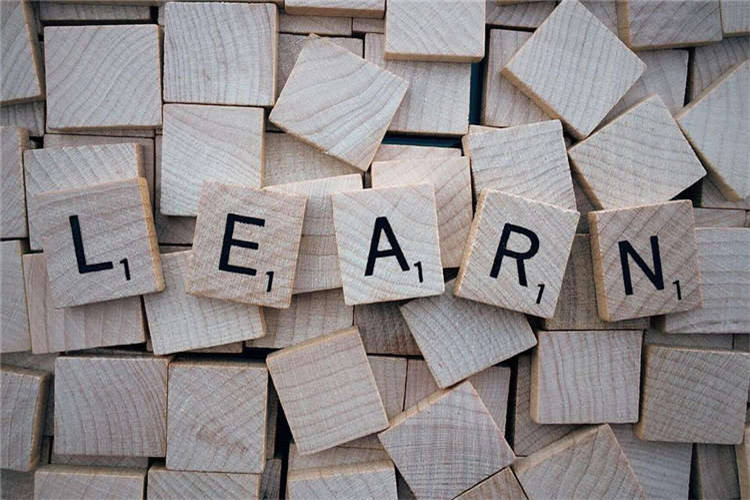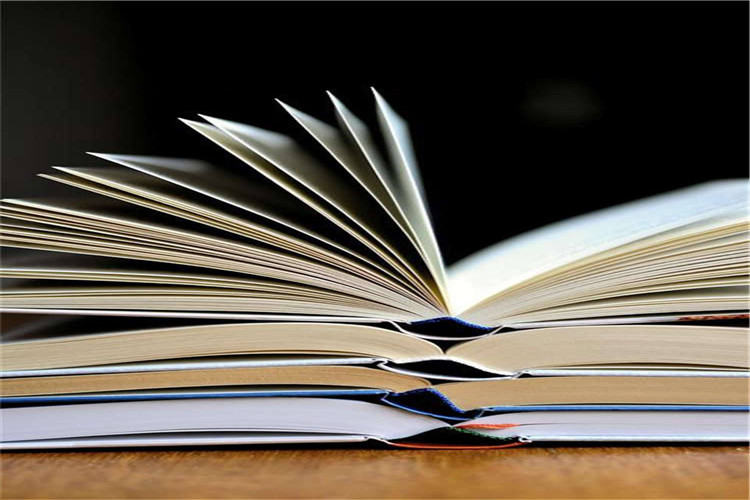对谈|如果“反对”疲乏了呢?尝试赞美、缝补这个世界
2024年5月初,由《合流》诗刊组织的“青年华语诗人交流计划第三弹:单丝不成线”在线上举行。本文是第三场对谈“宇宙或屋宇?——太遥远的和太近的”的节选,来自各地的青年诗人交流了各自的写作资源和脉络。文字稿由李盲、拓野整理,经对谈者审定。
沈嘉昊:我想先邀请大家讲讲自己的写作契机以及分享一些写作资源。
萧宇翔:如果有某些诗学意义上,能够跨越偏见、隔阂的“压缩时空的线”,我想大概就是嘉昊所说的“写作资源”、“美学资源”。我大概重整了几个,至少是在我的同辈们之间有共识的资源。我的同辈包括琬融、宇轩、驭博等等,他们都有在《合流》的“青年华语诗人交流计划”上发表诗作。我整理出大概四种写作资源。
第一个是“翻译资源”。 我觉得翻译资源跟诗学资源要放在一起谈。“翻译资源”很简单,比如说像曹驭博的办法就是纵览一百年来所有得过诺奖的诗人,大量地阅读这些诗人被翻译过来的诗作;比如他就很喜欢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默。而我自己最喜欢的是俄罗斯诗人布罗茨基,后来他被放逐到美国了。我记得宇轩对墨西哥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也有一些研究。
那么,为什么“翻译资源”要跟“诗学资源”放在一起谈呢?因为,我认为不能够点状地阅读这些诗人,他至少要能够起到某种系谱学的作用。就是说,当我们读白银时代诗人,譬如说帕斯捷尔纳克、曼德尔施塔姆、阿赫玛托娃。我们需要纵览式地阅读,就是将点连成线、线连成面地去理解那个时代的诗人们,理解他们与苏联的关系、与他们的前辈们的关系。譬如说,他们作为“阿克梅派”的成员,与上一代的未来主义、象征主义的诗人们之间的代际关系是怎样的?或者说,当我在读布罗茨基时,我能不能从“流亡诗人”的面向去了解他,借此也去深入了解米沃什?
所以当我在读杨牧的诗时,我会关注杨牧与英国浪漫主义的关系、与英诗的关系。他对英诗有一个非常详尽的梳理,就写在他翻译的英诗汉译集里。我认为杨牧最大的特征是,在他句法中有一种连绵感、连贯性、整体性,显示出他独有的有机发展章句的方法。这个东西怎么来的?我详尽地研究过杨牧对英诗的考察后,发现它其实是从乔叟对英诗格律的改造中借来的;乔叟推进了英诗无韵体的发展,但无韵体也并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乔叟从意大利诗歌的韵体中借过来。在此之前英诗有自己的一套格律,但在乔叟之后,他把英诗的体式扩展到了一个既有限制又有自由的一种状态;英诗在形式上和语言上都被扩充、更新了,英文也变成了一个拥有自己体式的语言。杨牧很看重这一点;他对汉语诗的贡献,也是从这里汲取的;等于说,他在这里发现技术与语言之间的关系——技术当然指的是修辞技术;而语言,指的是它的改革与以及相应的文化、历史背景。
萧宇翔的诗集《人该如何烧录黑暗》书封
另外两点是“古典资源”和“对手学科”。“古典资源”很好理解,比如说杨牧就对六朝的古典文学非常有兴趣。而我自己也有一些诗也是出自古典典故,比如《万华行》就出自蒲松龄的《促织》。“对手学科”也很好理解,譬如说我们刚刚谈论的“媒介”。再譬如说我受教于小说家吴明益,他就经常跟我们强调“对手学科”的重要性;就是说,我们能不能不附着在文学–文化相关的知识链条里面,这条链会不会某种程度上是封闭的。我们可以从文学的对手学科里汲取营养,比如说科学、自然生态。我记得美国诗人斯奈德就是这样的写作者,而我对他也很着迷。
以上就是我总结的四个资源。所以我在阅读在座几位的诗时——拓野、嘉昊、李盲、匡哲——我也是在用某种“诗学资源”的方式在看,就是在考虑诗歌中的修辞技术及其背后的文化观。比如说,我就蛮好奇,匡哲是不是读过不少史蒂文斯或者臧棣的东西?我这么问,是因为我发现匡哲的诗有很多用“假语法”做出来的譬喻效果,而史蒂文斯也是使用“假语法”进行形象类比的高手……而综合看拓野、嘉昊和匡哲的诗,大家似乎都对“悖论”、“博学”有着不同程度和层次的着迷,我觉得这是一件很诗学的事。
林宇轩:在这个活动开始之前,我和宇翔稍微讨论了一下今天对谈参与者的作品。我觉得有趣的是,这些作品所呈现出来的美学和我们平时阅读的作品蛮不一样的。无论是诗行的长度、内容的复杂程度,还是回行的技巧,都与我们熟悉的方式有明显差异。我们讨论后有一个小小的结论,这可能和文化背景、历史脉络以及社会氛围有一定的关系。
我注意到,除了诗行长度的不同,还有一种形式,我个人习惯称之为“定行诗节”,也就是每节诗的行数保持一致,比如两行一节、三行一节等等。我不确定这是不是年轻一辈诗人们更常用的方式,但近年来,这样的作品似乎越来越多。
可以延续刚才宇翔的讨论来看,除了这些资源外,在篇幅上的企图,也就是怎么规划诗歌的篇幅,也很值得探讨。
……
然而,我观察到,这次对谈中的大部分诗人们的作品似乎与这种流行趋势截然相反。诗歌篇幅较长,内容复杂,与网络上流行的那些作品形成了鲜明对比。……我认为通过长诗的方式,既可以回应艺术性 ,也可以在文学生态中挑战以小说为主导的场域规则。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不知道其他人是否也有类似的发现,可以作进一步的对话?
沈嘉昊:关于“定行写作”,从我的观察来看,这种形式在当代汉语诗歌写作中是很常见的,尤其是自“五四”之后,很多诗人也采用过这种形式。比如朱湘,他有一首很有名的诗,每一行的字数、标点符号都是一模一样的,整体呈现出一个非常规整的长方形。我们在写作中,依然有对古典诗歌形式的执念和迷恋,比如绝句的形式,这也是汉语诗歌的一种遗产。我们对形式整饬似乎有一种迷恋、怀旧。同时,诗歌是分行书写的,三行、四行或两行为一个隔断的这种分段的形式,对于青年写作者来说,有助于更好地排列文本内容递进、密度,分配思考的进程,以及对所书写事物的推进。大陆青年诗人,有很多采用这样的写作形式。
随着网络的兴起,带动了一批新兴的写作者。我这里可能有一点“卫道士”的心理,在我看来,这些写作者与其说是诗人,不如说更像是文案写手。他们的创作更多是一种纯粹情绪化的表达。观众在阅读这些作品时就能获得某种氛围感,或者某种很简短的体验。这种写作与短视频传播的快速信息传递机制是相同的。相比传统的严肃文学,这类写作缺乏深度,文本内部的密度和内容质量也有所不同。所以,我更倾向于他们是消费社会的产物,更多是制造吸引人眼球的产品,或者仅仅提供一种氛围和情绪;而不同于严肃的写作者,一直在推进如何用更少的字词去刻画更大、更深刻的事物。
长诗可以说是当下对这种“快消型”写作的一种抵抗,或者更像是严肃文学内部对“小”写作的对抗。因为长诗和短诗不仅体量不同,背后也有本质的差异。短诗写一个特定地方发生的一个小事件,或者看到的一件小事物;而长诗则可以探讨更为广泛的主题,涉及历史、时代现象,甚至多维度的思考。正如宇翔提到的,长诗可以面向某个主题,比如科幻,或者更宏大的方向。相对于短诗,长诗可以容纳更多的内容和复杂性。
梁匡哲:刚刚听到宇翔讲布罗茨基、讲西方诗人的理论时,我想到自己大概十年前也是疯狂地在吃这些西方诗人的东西,为的就是要对抗当时香港的一条诗歌传统:“赋体诗”。“赋” 源于《诗经》里的“赋比兴”; “赋体诗”在2000年左右变得非常流行,诗歌非常平白如话,非常平淡、生活化的诗。这种诗风来自上世纪80年代香港本土诗人和余光中的论争,那个时候余光中在香港任教,也带来了“余派”,形成了一脉中国化的意象诗。而本土诗人的代表就是梁秉钧,他希望走出一条“第三条路”,由此形成了香港本土的、生活化的诗歌风格。即与现代主义对抗的“本土主义”。
这个风格到了2000年左右,也就是我的中学时期,我和荧惑他们这一批人开始觉得,这种原本是对抗“余派”的诗风慢慢演变成了霸权。因为这种风格真的很沉闷,没有什么特别的。所以我们要找一些不同的东西,比如说除了找痖弦、商禽、洛夫、杨牧以外,还有很多当时台湾地区比较年轻的诗人,比如说林禹瑄。那个时期,我们还读了很多西方的现代主义诗歌翻译。香港有一些非常重要的翻译家,其中黄灿然对我们影响深远。那时候我们读他的那一本《必要的角度》,是一本评论集。那时候他在翻译策兰、布罗茨基、米沃什、毕晓普等诗人,很多都是转译自英文。所以内地的资源其实也很重要,那时候很多简体字的译本能在香港买到。我们借助这些资源,去对抗那种所谓的本土化、生活化写作。
《必要的角度(增订版)》 ,黄灿然著,上海文艺出版社·明室Lucida2024年8月版
当然,现在我不再像当时那样极端地对立于生活化写作了,因为后来我也意识到,一些西方诗人,比如斯奈德,他的写作也源于禅宗和生活化的元素,并且从中提炼出诗意。但那个时候确实偏好那种高度压缩的意象、悖论修辞的现代主义诗学,去打破“赋体诗”的独大。
我们那时候真的是“饥饿状态”,想尽可能多地吸收不同的资源。当然,我们不像宇翔和宇轩那样有系统地去思考,比如浪漫主义和杨牧诗歌之间的关系——我们没有这么详细,而是“去脉络”地阅读这些诗歌。但我们确实很直观地觉得这些东西很新奇、很刺激。比如,悖论、矛盾修辞这些手法;比如现代主义诗歌。这些都是我们想用来反对生活化写作的工具,以此彻底与之分道扬镳。
……
拓野:注意到很多朋友都在写长诗,所以借机谈一些有关长诗的结构和义理的问题。我写了一首诗叫做《媚道诗》,那个是写山水的,但我也是用了一个佛教的结构,就是八苦,生老病死,爱别离等等,然后就分成八段,每一段可能是对应这么一个苦的这么一个idea。我其实还有另外一首诗也是干类似的事情,它是写一个科学家,我们都认识,叫达尔文船长,他的故事。然后我的第一句叫做“烦恼的我不想再做人,突变为小猎犬号吧”,然后出现在什么大海上之类的。当年达尔文搭乘的那艘船就是小猎犬号,或者说叫贝格尔号。那首的话,就想每一章也是用十二因缘里面的一支作为隐线索。
这里面其实有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这些结构它其实是被古人咂摸揣摩,把玩了几千年,然后我们再去用它的时候,合法性和有效性究竟在什么地方?我有个朋友叫李舒扬,她以前跟我探讨过这个问题,就是说,义理可能是不同于结构的,比如说有个诗人叫朱朱,他有一首诗叫《清河县》,它里面其实既用到义理也用到了结构,那种结构其实指的就是最基本的结构、空间结构或时间结构。比如说你站在舞台的中央,舞台下面的人从不同的方向指向你,这就是一个从四周到中心的这么一个包围的结构。然后朱朱可能就把这么一种空间的结构,或者说视线的结构运用在他的诗里面。时间的结构其实写诗更方便叙事诗,因为你一个诗想写长,你难免要借助一些叙事的因素,那么时间性就一定会被带进来,但是义理的话和时空结构又有点不太一样,它其实是人后天捏造出来的,比如说八苦,比如说色、受、想、行、识这些五蕴,它们是被人们捏造出来的事,但是它又包含了某种真理性。但对于真理性,其实我们是没有办法真正的把它说清楚的,我们就是无法言之,只好暂时拿了这些义理的结构去言说它,比如说大学里面的八条目,诚心正意,什么格物致知之类的。这个东西它是有它历史学上面的发生,它就不像时间结构和空间结构那么纯粹,好像可以运用在所有的诗歌里面。所以我觉得像这种佛学入诗可能就有个问题。其实你得跟他去做一个很艰难的搏斗,我们才能把它用得很好。一定程度上,他们被那么多宗教,那么多哲学家,那么多文学家,几千年的阐发已经形成了很多陈词滥调。但另外一方面我们又能感觉到,这里面有一种不同于时间结构空间结构的一些魅力,有一种还有我们之前说的那种所谓的诗人,那种天真的言之凿凿。好像我们虽然不是圣人,但是我们就是凭着一腔热血,或者说一种赌性,我们说出了这几个词,然后在我们这一首诗里面把义理的结构置入,他们就好像我们打到了河流里面的一个一个坚硬的木桩。之后,我们其他的思想,其他的思维,其他的诗句则是好像一个弹球一样在这个木桩里面弹来弹去。木桩是固定的,但是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的思维和这些固定的东西,它们发生化学作用之后,最终产出来的东西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所以我觉得,好像我们是用了那种非常僵硬非常死板的这么一些名目,去写这么一个东西,但是其实结果还是挺未知与奇异的。
萧宇翔:刚刚我们讨论到“反对的姿态”,尤其在青年诗人中,是一种文学的基本态度,也是我们在文学中学到的基本姿态。但我非常欣赏像扎加耶夫斯基这样的人,他是波兰流亡到美国的诗人;或者里尔克。他们身上有一种诗人的气质,这种气质是维系他们从中年到晚年持续写作的气质。我觉得很有趣的一点是,他们到了某个阶段,似乎对“反对”感到有些疲乏——如果在文学中只有不断地反对,那么如果“反对”疲乏了呢,“反对”被消耗了呢,“反对”在某一处逻辑打结了呢?那么,“反对”的反义词就是“赞同”, 作为一个诗人,我们可以赞同什么?
这里我想引用胡塞尔的演讲《欧洲文明精神的危机》,这篇演讲发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米兰·昆德拉也曾在《小说的艺术》一书的开篇引用了它。胡塞尔在演讲中提到,自希腊时代以来,我们开始把描述人类的任务交给各种专家——譬如说谈论公共性灾难时,我们过度依赖于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民族学等学科的专业术语。我们对人类的想象变成某种大树的枝蔓在生长,或者蚁穴在扩张,它过度细分了对人的理解。根据胡塞尔的说法,这种过度分科造成了四百年来人文精神的弱化,人类也因此失去从全景视角观看人类自身的能力,以及描述人类的激情,胡塞尔称之为“存在的悖逆”。 在昆德拉看来,文学可能是唯一保留着描述人类全景的能力、表达对人类的激情的领域。像是某种缝补,像是扎加耶夫斯基著名的诗《尝试赞美这残缺的世界》所说,尝试赞美、缝补这个世界。或者用我们今天的语言来讲,像是一条尝试压缩时空的线。就是在这么一个过度细分、后现代主义盛行的时代,如果还存在某种具有全景式的统摄力,那它会是什么?或者说,如果文学作者是一个主体,那他是否能保留某种形而上的坚持?
《小于一》,[美] 约瑟夫·布罗茨基著,黄灿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1年1月版
就像我们刚刚提到了布罗茨基的《小于一》,表面上他是在介绍俄国白银时代的诗人,实际上他在重建一种语言的形而上学——语言本身的形而上学,即语言先于一切、美学先于伦理学。而语言本身能造成什么效果?他说是一种“思考的加速器”,一种思维的提升;因为语言先于我们的存在,它能带领我们到达一个原本无法预见的地方。这种想法在过去似乎是被祛魅了的,因为我们相信我们能控制对语言的所有的操作,不管是局部还是全景,但布罗茨基认为其实不然。其实他把人类变得渺小,语言变得巨大。就像太空人在回望地球,看到人类的渺小、历史的渺小,看到了火山喷发、洋流涌动、森林燃烧。他们从宇宙中看到了地球这种能力正是胡塞尔所提到的全景视角,而布罗茨基的写作就是对语言全景视角的坚持和辩护。我还想到其他跟《小于一》类似的作品,比如说米沃什的《诗的见证》和帕斯的《泥淖之子》,这三本是尽量要通读的书。
《诗的见证: 哈佛大学查尔斯·艾略特·诺顿讲座,1981-1982》,[波兰] 切斯瓦夫·米沃什著,黄灿然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贝贝特2016年10月版
在这样的诗学理念下,我倾向于写长诗。正如拓野刚刚所说,长诗这种密度、分配、推进非常匀称,而且具有可读性的创作方式,能够让作者的主体凸显出来、让语言思维被放到一个全景的维度,这是一种对诗歌的集大成的挑战。但是我对当下的流行写作并不抱有深刻的厌恶,支撑我写作的其实是一种对人类的描述激情,像里尔克、奥登、沃尔科特、卡森这些大诗人一样,保持一种赞美事物的姿态。
《泥淖之子: 现代诗歌从浪漫主义到先锋派(扩充版)》,[墨西哥] 奥克塔维奥·帕斯著,陈东飚译,广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1月版
沈嘉昊:这些光辉的、过去的诗人形象,可能他们是我们反对的一部分,但是实际上他们也锚定了我们过去写作的一个基石。可能“反对”本身不代表完全的、绝对的反对,而是说我们反对的是一种风尚,而不是整个过去。我们同样也是认可过去,比如说臧棣等人的一些对过去上世纪80年代到新世纪后的思考,同时这些思考也为现在的汉语写作打下了基石。
……
萧宇翔:我们所受的诗歌熏陶其实是很相像的,身在台湾地区写作,我们也读大陆的诗,比如朱朱、欧阳江河、王小妮、张枣、顾城等等……然后我们也读翻译诗,帕斯、米沃什、布罗茨基……我们的阅读有相当部分的重叠。但有趣的地方就在于,我们的阅读如此重叠,竟然每个人写作方法都完全不一样。
……
我发觉“风格的焦虑”已经完全不成为焦虑了,就是每个人所学的哪怕是一样的,但是每个人所钟爱的往往是独特的。这些构成了一个一个坐标,连点成线,画线成面。像我就偏爱布罗茨基的诗、坂本龙一的音乐……这些组织在一起,变成一个独立的自己、独立的状态。我觉得已经摆脱了那种焦虑,包括对养分的焦虑、来自历史意识的焦虑。
沈嘉昊:对我们来说,风格焦虑其实是无时不刻的。但真正在困扰着我们的,其实可能是这种“风格的焦虑”以怎样的方式呈现出来?艾略特认为,说摆脱“风格的焦虑”需要拒绝一个规范式,一个我们所围绕着的东西;我们需要开阔,需要面向更广大的语言以及面向更广大的世界。
……
为什么我们这么多的资源重叠,但是写作出来的东西是如此的不同?我一向认为人和人之间它是隔绝的。虽然呈现出来不同,但如何发展下去,可能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如何把我们经过自身能够产出的东西源源不断地呈现出来。然后,我们可以面对无限多的事物,包括宇宙和物欲之间的所有的事物。我们怎么去面对它?可能是一个终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