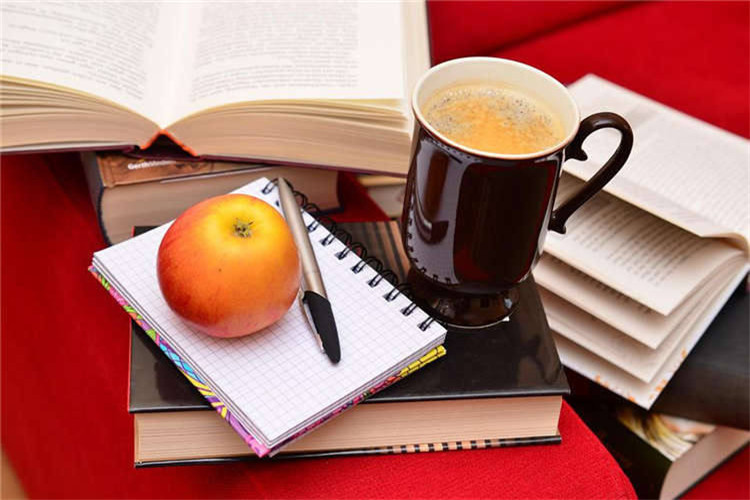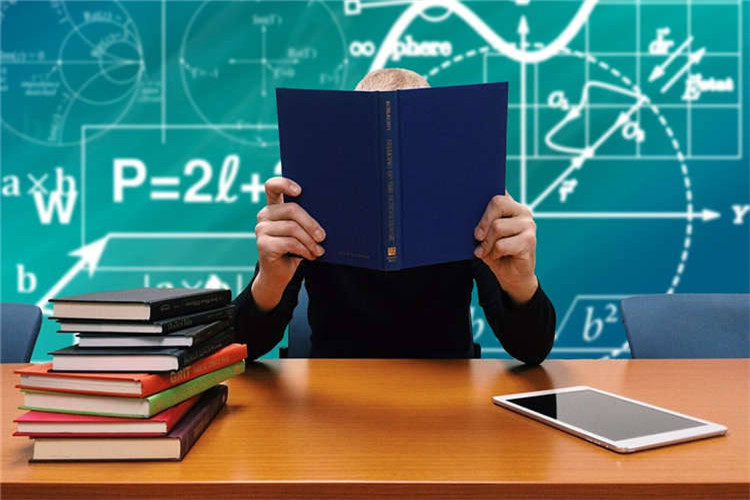专访|梁鸿:写梁庄写我们共同的生活
“回到梁庄,实际上是回到我的另外一部分。”10月在河南中牟举行的三联人文风土论坛上,作家梁鸿讲述了她写作和生命中“作为家乡的河南”。对她来说,家的概念随着距离越来越远而不断拓宽,又在一次次的返回中变得具体。
在中牟的一家咖啡馆里,我们和梁鸿的采访也从“家”的话题开始。咖啡馆位于当地的一处新兴居住社区,本地的生活和新鲜的城市设计理念在这里融合。和众多的小城一样,中牟连接着河南的乡村和城市,自然地呈现出某种中间态。梁鸿的行程有点紧,采访之后,她要赶去郑州美术学院准备这天下午的论坛,第二天一早再出发回老家。
梁鸿
“我先坐高铁到邓州站,然后坐车到城里,我姐姐她们都住在那里,再从县城回梁庄,”说起老家,梁鸿特别开心,如今,她回老家的频率大概是一年四五次,交通越来越方便,从郑州出发的话,大约两个半小时能到家。1997年,梁鸿进入郑州大学攻读硕士,2000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攻读博士,毕业后继续从事文学研究,如今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任教。在不断地去往更远的世界时,梁鸿意识到,她精神的源头始终在梁庄,在家乡那条名为“湍水”的河与河流边上的那些土地和树木里。她说,关于梁庄的写作是一次回家,是重新与自己的家发生情感关联的过程。
2007年,梁鸿决定“要回家写点什么”,她回到家乡梁庄,她返回家乡,重新认识身边的人和他们的故事,于是有了《中国在梁庄》,以及后来的《出梁庄记》与《梁庄十年》,组成了很多人所熟悉的“梁庄三部曲”。在这些关于家乡的非虚构写作里,个体的故事一个又一个从他们自己的叙述里浮出,一张村庄里的关系网也随之浮现。这张网随着梁庄人出乡打工而伸到城市,或者换句话说,梁庄是中国诸多乡村里的一个,而城市无论看起来多么迥异,总是它们的延伸。在梁鸿看来,写梁庄的日常生活,也是在写每个人共同的生活,从那里折射出一幅当代生活的全景,它如何分崩离析,又如何重建自我。就像她写《出梁庄记》的意图:“我关注梁庄的进城农民与梁庄的关系,他们的身份、尊严和价值感的来源,由此,试图探讨村庄、传统之于农民,也之于我们这样一个生存共同体的意义。”
在“梁庄三部曲”里,“我”的视角始终挥之不去。重返梁庄的梁鸿好像总是处在旁观与参与的矛盾里,而在文字里,她对于两种身份的纠缠也总是无比坦诚。在书里,她坦言身为知识分子,有时候不确定该“重返”到哪里,她会反思,“你的悲悯贬低了他们的存在……在貌似为梁庄人鼓与呼的悲愤中,梁庄再次失去其存在的主体性和真实性。”
“主体性和真实性”是梁鸿努力想让她的写作对象所获得的东西。无论如何,写作者无法摆脱自己的视角,但至少要保持真诚。如今,梁鸿文字里的梁庄还在生长着,而她希望,自己可以和梁庄一起经历“生老病死”,共同完成一部生命的长河志。
城市也许是乡村的延伸
澎湃新闻:对你来说,郑州这座城市和你的家、你的家乡是什么样的关系?
梁鸿:我觉得对于我来说,郑州可能还是我家的一部分。我从老家出来,在南阳读了大专,之后自学本科,再到郑州大学读研究生,那时候也觉得是离开家乡了,因为你对家的概念是从老家来看的。后来又来到北京,觉得郑州好像也是家,随着你离家乡越来越远,你对家乡的概念也在不断地扩大。我在郑州呆了四五年,郑州对我来说还是非常亲近的,因为你还在你的文化圈,你的说法方式、行事方式,周围人的性格也都还是河南人的性格,所以我觉得还是比较轻松的。
澎湃新闻:你会怎么看城市和它周边乡村之间的关系?
梁鸿:中国的城市其实发育得比较晚,很多城市可能有点像“大乡村”,比如从我家到我们县城,就是路宽一点,楼房多一点,生活方式还是亲属式的,人与人见面的时候,“你家叔叔爷爷是我的什么人”,第一句话会像这样攀关系,很有意思。县城就像一个大的家族场,整个郑州或者说整个河南都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在中国,起码在内陆,城市的发育不是完全脱离乡村,实际上还是乡村的升级版。当然以后随着城市的扩张,可能会有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在诞生,在成长,但是它跟乡村的关联仍然是丝丝缕缕的,我们不评价它的好与坏,但是这种关系一定还在。
澎湃新闻:你在书里写到了梁庄的年轻一代,他们离开家乡到城市打工,城市不是自己的家,另一方面乡村他们而言也没有归属感。这些年轻人是怎么看自己的家乡和归属的?
梁鸿:这一代年轻人中有很多在很小的时候就跟着父母打工来到城市,然后到了初中的时候再回到当地。比如我书中的阳阳就是这样,小时候一直和父母在青岛生活,到了初中因为没有学籍,又回到我们镇上寄宿。你说他对梁庄的感情到底怎么样?他对梁庄也是一个符号化的认知,他当然知道梁庄是他的家——他家的房子在那盖的,他奶奶还在那生活,他的父亲母亲每年回去看他们——但对他本人而言,他并没有任何生活习俗,没有小时候我们和父母之间那种无意识的陪伴,所以很难看到他对梁庄有多大的归属感。你也看不到他对青岛有多大的归属感。对于他们这代孩子来说,可能没有那种固定的家的概念。但是有一点,他的土地还在这个地方,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一个抽象的家永远在梁庄,至于他生活在哪其实并不重要。我觉得当代的青年可能就是这样,这和我这一代是完全不一样的状态。我15岁以前没有离开过家乡,我们与村里的那条河,村上的那棵树,日日相见,那种情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澎湃新闻:你在“梁庄三部曲”里写了许多梁庄女性的故事,她们的名字和生活常常依附在其他的男性亲属上,在公共生活里没有话语的位置,很多女性仍然要努力地找回主体性。联想到今天对于“女性出走”的探讨,在你看来,对于农村女性来说,城市是她们唯一的出口吗?
梁鸿:我觉得这种处境不只是乡村女性的,是全世界女性共有的。我们一定要知道,女性观念的这种无意识,在全世界任何一个阶层都一样的。可能乡村女性受到的压抑更多,所以更需要被提出来,被看到,被理解,但并不意味着城市女性面临的境况和她自身的意识就更先进。我们的文明状态几乎是相同的,虽然中国经历了更加漫长的封建时代,但实际上现代化以来,你会发现西方女性的地位也并不见得有更好的状况。我们都需要一个新的观念的重新注入,这是全世界女性所共同面临的一个课题,而不单单是中国的乡村。
写作是与知识的双重辩证
澎湃新闻:在《中国在梁庄》里你写到,“重返梁庄的第一冲动不是想揭示梁庄的真实,而是为了寻找一种精神的源头,以弥补自己的匮乏和缺失”,你觉得对于今天的这一代年轻人来说,这种精神的源头是否仍然重要,或者说像“梁庄三部曲”这样的写作会帮助他们找到这种源头吗?
梁鸿:我觉得很难,因为每个人的精神源头和他们自己的生存有关,可能读了这几本书会有一些感触和新的理解,你看一本书可能会激发你内心的情感,但是因为你没有过这样的生活,很难真的形成一种源头。我觉得写梁庄是希望大家有一种理解力,对乡村,对生命的流逝、每个人的故事的理解,但是很难真的对别人的价值观重新塑造,只能说会有某种感召或者激发。
澎湃新闻:之前你说过文学具有致力于探索一个人存在的状态,人与时代、文化的纠缠,很多形象在很多年前已经先验地存在于文学里,作为新闻事件重新来到我们生活内部。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充当了“预言家”的角色。现在你会怎么看文学写作和“此时此地”的关系?
梁鸿:我们都有一些先在的观念,我们生活在某种文化氛围里、从小接受这种教育,这些日常的观念相应地也就是我们的偏见,因为它是固定的,是无意识的,我们很难去察觉到。文学也是一样,当你拿起笔的时候,乡村已经存在100多年,从鲁迅的《故乡》甚至更早就已经存在了,你是很难不受它的影响的,但是作为一个写作者,你又有义务去摆脱它。一方面需要深厚的知识支撑,包括每一代人怎么写故乡、写乡村,以及那些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怎么去理解乡村,都要多了解。但另一方面你要摆脱这些观念,用崭新的眼光来看待乡村。这是一个双重的辩证——你既要拥有一个知识体系,同时又要摆脱你的知识体系,这是非常艰难的。但不管怎么样,一个作家需要去做这样的努力,用一种崭新的眼光去理解你所看到的现场,你所看到的人。在这个意义上,故乡已经在你心里面存在100多年了,梁庄在你心里面也存在100多年了。另一方面,作家必须要去摆脱那些眼睛背后的视野,那就看你的博弈、你的辩证到什么程度。
我觉得“梁庄三部曲”当然并不是最成功的,但是起码在写作的意义上,可能它有一点点新意,我觉得这已经非常难得了。从《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到《梁庄十年》,我也在慢慢找一种角度和方法去写,也许有一天我会呈现一个崭新的东西,这个过程是很重要的,也是一个作家在不断成长和嬗变的过程。
澎湃新闻:你在书里说到写梁庄经历了一个从“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再到“看山是山”的过程,是不是也对应了刚才所说的这种写作上的转变?
梁鸿:是的。意思就是你从一个复杂的背景里抽脱出来,重新去看,和你直接去看是不一样的,它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辩证过程,再用一个童真的眼光去看,这种童真背后有很多东西,这需要时间,需要思考的长度,各方面不断的磨炼。
澎湃新闻:刚刚说到需要时间,“梁庄三部曲”中间有一个10年的跨度,你在书里也写过想以“梁庄”为样本做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持续的观察。对于记录一个地方的变迁这样田野调查类型的写作,是不是10年会是一个比较好的衡量的跨度?
梁鸿:其实10年是一个大致的说法,对于我来说,可能更关键的是它的持续性,它的连续性。我已经想到了梁庄系列的最后一句话,我要写“梁鸿即将死去”,我和梁庄一起生老病死。我希望能给大家呈现一个村庄志,一起感受这种长河般的生活。新的生命诞生,也有人慢慢地老去,我也会慢慢老去,就像一个纪录片一样,我希望通过文字来留下这些东西。
澎湃新闻:是否可以说,文学和新闻不一样,新闻需要时时更新,但是文学是要经过一段时间去回看当时的事情?
梁鸿:文学讲究的不是即时性,更多的是背后的东西,所以它有一个时间的长度,它看中的更多是背后潜移默化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文学实际上是没有那么紧迫的,不像新闻有一个呈现突发现实的意义。文学更多呈现的是事件背后生活的存在,一种人性的东西。
澎湃新闻:关于文学和现实的关系,之前你说处理材料的时候要经过隐喻再呈现给大家,现在也是这么认为的吗?
梁鸿:其实我当时写的“隐喻”并不是实在的隐喻,而是说只要经过语言的输入,语言的书写,我们面对面说话变成语言之后,本身就是一种隐喻的存在。语言本身就是关于世界的隐喻的存在,我们已经经过转换了,但是怎么样让隐喻和现实发生关联,让隐喻和现实之间有一种对应,这是需要作家去不断琢磨和思考的。
澎湃新闻:在梁庄的写作里,你既有外部的视角,也有作为梁庄人的内部视角,对于更多的田野观察以及非虚构写作来说,你觉得怎样可以有更加真诚的切入?
梁鸿:我觉得梁庄比较独特,因为它是我的家乡。我写其他的非虚构文本怎么办?我得找一种新的写法。所以我觉得对于一个写作者而言,你对于现实的了解有多深远很重要。了解和理解是两个概念,了解是现实本身,理解是现实背后的东西,它会更多地决定你写作状态的深度。真诚当然是你的前提,这是另外一个概念,但是你对现实本身的多维度性、它背后更深远的东西,更能决定你的写作。情感当然是重要的,我对于梁庄是有情感,但是对于其他东西不一定非要有情感,可能需要知识的进入。我说的真诚是当你面对现实的时候,你得有一个真正想了解的愿望,有这种好奇和热情,而不是为了写而写,那样永远写不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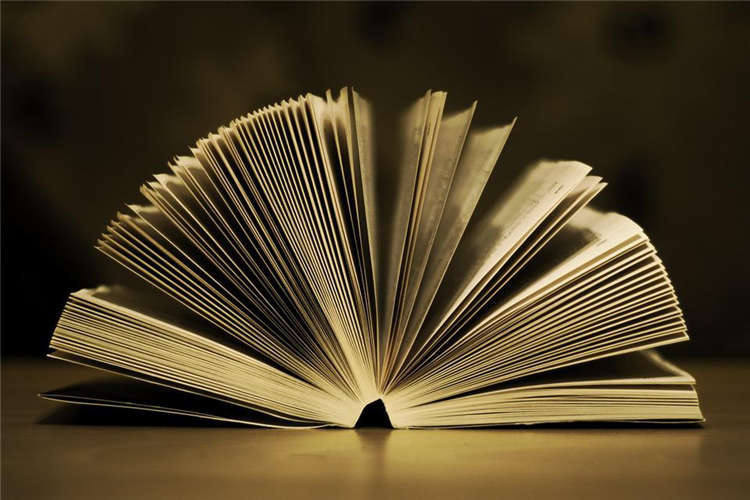
![鑫豪保险柜售后服务电话[维修客服号码]-《今日汇总》探秘安全之王:哪款保险柜真能傲视群雄?](http://cp.dufengkaoyan.com/zb_users/theme/weibolees/style/zsimg/86.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