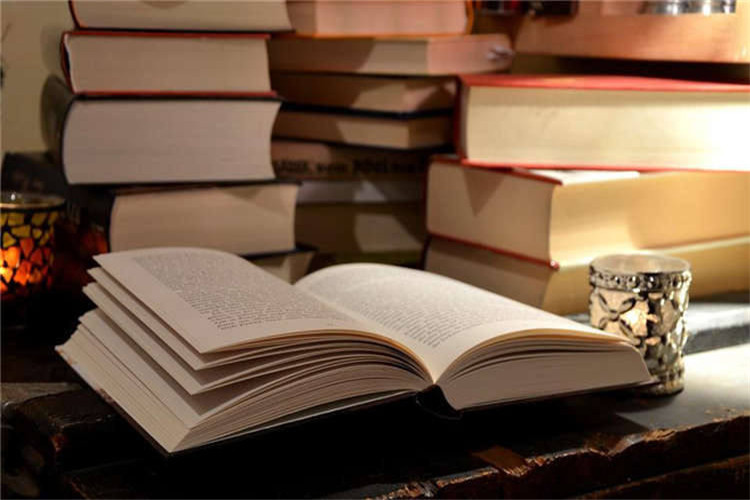口述|张纯如母亲张盈盈:我希望年轻人能拿出勇气,接下纯如的火炬
2004年11月9日,作家张纯如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她才华横溢,因《南京浩劫:二战中被遗忘的大屠杀》一书声名鹊起,以“一个人的力量”极大地推动了全世界对南京大屠杀的认知,却在36岁时受困于抑郁症而选择轻生,令人扼腕。
斯人远去二十载,澎湃新闻·私家历史约请张纯如的旧友、母亲,撰写文章、口述历史,纪念她离世20周年。
张纯如,这位无法忘却历史的女子,不应被历史忘却。
一
我的父亲张铁君1899年出生在贵州贵阳。祖父是清末驻扎在云南、贵州的武官,当时那里是相当野蛮的地方。由于他是汉人,所以并不受朝廷信任。那个时候已经“闹革命”了,祖父被人诬陷说参加“革命”,被召回北京。从贵阳到北京,他走了好几个月,到北京不久后就吐血而死,那年我父亲八岁。
父亲上面有个大哥,然后是二姐,他还有个妹妹。祖父的第一任太太没有孩子,他们叫她嫡母。那个年代如果没有后代是可以再娶的,祖父的第二任太太也没有生孩子,而且死得很早。第三任太太生下了这四个孩子,我父亲是其中之一。祖父死在北京后,我父亲的亲生母亲去贵州一个叫贞丰的地方想把一些属于祖父的地要回来,结果地没有要到,人反而被害了,死在了那里。那年我父亲九岁,他的亲生父母就都去世了。我父亲经常对我们说:他八岁丧父,九岁丧母,成了孤儿。
但是他的嫡母还在。祖父是个小官,还有一些财产,主要靠典当东西过日子,先把原来的大房子卖掉换成小房子,又把一间房间租出去,结果租房的人比他们还穷,所以也收不到租,慢慢的一餐不够一餐,经常饿肚子。父亲十几岁的时候,他的妹妹得了肺病去世了。他大哥已经出去参加孙中山的革命了,二姐是女人,那时不能出门,只有他陪着嫡母去当铺变卖家中一些东西过日子。日子过得相当凄凉。
父亲从小就勤奋好学,上学的时候因为没钱买书,只能用人家写过字的纸的背面去抄借来的书,他说因为要抄书,反而他书读得比别人好。那时的贵州,他周围很多人都在抽鸦片,父亲很早就意识到毒品是危险的——他就在这种又穷困又恶劣的环境下自学出来的。
后来革命成功了,大哥打仗回来,结了婚。但是他作为一个士兵的收入很微薄,没有办法养活一大家人。于是嫡母就和父亲去投奔云南昆明的一个亲戚,这个亲戚家境稍微好些。父亲在亲戚的帮助下,在昆明上了中学。父亲非常聪明,记忆力也好,很会作诗作词。
高中毕业后,父亲去了云南蒙自做事。他跟一个给报社写文章的记者相熟,也经常投稿,对报纸很感兴趣,看到很多上海来的消息。当时蒙自外界的消息比贵阳来得还要快,据说上海的报纸可以走海运通过越南的河内运达蒙自,去贵阳反而不方便。父亲突然发现世界这么大,他的诗作还投稿到上海的报纸上发表过。
后来父亲又从蒙自回到贵阳,把他的嫡母安顿好,跟一个同伴一起从贵阳出发,去东部大城市找机会发展。他们是步行,有的地方要坐滑竿(轿子),碰见水就坐船。当时贵州有很多土匪,他们一群人一起走,前面的人说有土匪了,后面的人赶快把铺盖卷藏到一个地方,等土匪走后再把东西找回来。每到一个地方,他就跟同伴怀古,作诗作词,他读的书太多了,历朝历代在哪一个地方出了哪些文人武将,他都知道。每到一个地方,他不仅怀古作诗填词,还观察民间生活动态。
就这样走了几个月,他们到了武汉。举目无亲,父亲在武汉什么事情都做过。他唯一的本事是会写字,于是坐在茶馆里,看谁有冤枉,想上诉的,他就帮人家写状子。他还做过指挥交通的警察。父亲对底层的劳动阶级特别同情,也特别了解,他很早就看到了上层阶级对劳动者的压迫,一生都为这种不公平而打抱不平。有一天他经过一个教堂,闲着没事就进去听听。牧师说人人都有罪,父亲问了他很多问题,牧师回答不上来,他请父亲再来教堂辩论,又跟父亲辩论了很久,牧师还是辩不过我父亲——我父亲辩才很厉害的。后来,虽然父亲不信上帝,他们还是把他吸收进来,给了他一份工作,让他在基督教路德会的小学和中学教书,教文科。
父亲一面教书,一面拼命读书,读遍了各种主义学说,对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无政府主义”非常向往推崇。但接触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后,感到这是能救中国的主义,于是就追随中山先生,一生都是他的信徒。父亲还在武汉认识了很多朋友,比如陈立夫、张道藩、粱寒操,他在1926年加入了国民党。(我父亲在60多岁时写了自传《蘧然梦觉录》。他一生多彩多姿,如果想知道更多他的生平,可以看看他的自传。他的自传在生前就捐给了美国各大学图书馆,如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还有美国国会图书馆。)
1975年,张纯如一家四口与她的外公外婆合影
二
后来父亲去了上海教书,认识了我的母亲。父亲那时35岁,母亲才20岁,还是个学生。结婚后,母亲到日本去读书,父亲跟着一起去,到日本不久,感到中日战争要爆发了,又赶快回来。
我的大姐出生于1936年,哥哥出生于1938年,我出生于1940年,都相差两岁。1937年卢沟桥事变的时候,我父亲在南京。战事不利,11月他接到通知要撤退。当时我外公去世了,母亲领着一岁多的姐姐回老家办丧事,顺便把外婆和舅舅接上一起逃难。她正身怀六甲,怀着我的哥哥,挺着大肚子。父亲请人带信息到宜兴官林镇,叫母亲坐船由水路到芜湖和他会合。那个时候兵荒马乱,父亲等在芜湖码头,本来要坐的单位船快要开走了,他又等了三四天,对着每艘靠岸的船喊母亲的名字:“以白!以白!”奇迹出现了,母亲从一艘小船里伸出头来喊:“我在这里!”
一大堆难民都挤在码头要逃难,根本没有船可以容纳这么多的难民。后来,来了一艘船,父亲一直哀求,人家勉强答应,但是只能人上船,行李不能上船,因为船已经严重超载。结果父亲所有的诗文、书籍、跟母亲在日本拍的照片全都丢在码头上了,只留下姐姐需要的东西。当时只管逃命,其他哪管得了那么多。
一家人先逃到武汉,又从武汉逃到衡山。我的哥哥就是在衡山出生的,生完孩子母亲来不及坐月子,两个星期后就继续逃难了,经桂林、柳州,然后到达贵阳。都是一段一段的火车、汽车,每段都要转车,路途非常辛苦。在贵阳待了一年,父亲被召集到重庆,这样一家人就来到了重庆。
1940年,母亲生我之前两周,父亲把她送到当地最好的重庆宽仁医院待产。宽仁医院一边靠山,一边靠嘉陵江,父亲认为日本人不会来轰炸医院。结果没想到,父亲眼睁睁看着几十架飞机过来轰炸了江对岸的医院,医院着了火,他想母亲一定没命了。警报没解除,他就赶紧渡江跑到医院,发现医院大门被炸烂了,但所有的病人都被及时抬到防空洞里了,母亲安然无恙。
父亲吓坏了,把母亲转移到长江南岸偏僻的乡下——海棠溪东边山区一个叫青沟湾的地方,这里没有电灯,黑漆漆的,这样日本人不会来轰炸。生我的那晚,父亲走了12华里到黄桷桠请接生婆,雇滑竿把她抬回家里接生。生产的时候,没有电灯,要用灯蕊菜油点的灯,父亲说他点了好多灯,所以很亮。我一出生就哇哇地哭,眼睛很大,泪水盈盈,父亲就给我取名“盈盈”,是很满的意思。
我三岁就有记忆了。那时我们搬到重庆郊区覃家岗,住在一个农庄,周围都是田地,只有一条路出去。房子依山坡,附近有蛇,每年都要打死好多蛇。没有自来水,要去山坡下挑井水,倒进大水缸里,还要放明矾消毒才能用。生活很辛苦。
日本人对重庆实行所谓的“疲劳轰炸”,不让我们休息。母亲刚做好饭,轰炸机就来了,我们每个孩子都有一个小板凳,抱着自己的小板凳往防空洞里跑。后来有经验了,我们带上干粮,父亲还把行军床和桌子放在防空洞里。我们进防空洞有吃有喝,还能躺一下睡一下,别人都好羡慕,说我们的爸妈为儿女想的周到。半夜跑警报很辛苦,父亲把我们从被窝拖出来,穿上衣服就往外跑,很冷,防空洞里又很湿,一进去好几个小时不能出来。
父亲在重庆城里工作,我们住在覃家岗乡下,父亲每个周末回来看我们。每次回家父亲会带花生、糖果并在家里开茶会,告诉我们外面发生的事情,比如国民党部里发生了什么事情,美国、英国有哪些消息。他会很直白地讲自己的看法,我们也可以自由提问,问什么都可以,非常民主。有时候别人看到了还以为我们小孩跟父母一天到晚吵来吵去的——我们就是在这样一个很自由的家庭氛围中长大。
日本投降的那天,父亲还没到家,我们就听说了,到处都是鞭炮声。父亲回来了,大声喊说胜利了,带回一大堆报纸,上面都写着“日本无条件投降”。大家高兴非凡,准备回都,也就是回南京。但是父亲被社会部和文化部派到武汉接收日本人留下来的东西,父亲先去,妈妈和我们于1946年坐飞机从重庆到了武汉。那是我第一次坐飞机,声音大得不得了,每人发一个袋子,果然大家都在吐,我也吐。弟弟晕得一塌糊涂,下飞机的时候整个脸都白了,母亲还以为他要死了,后来才慢慢恢复。
我在重庆上的幼稚园,到了武汉开始上小学。一年级读完,情况就不太好了,内战的苗头已经有一些了。接着我父亲又被调到南京,印象中南京的收音机里一直在唱票,好像是李宗仁和孙科在竞选。那段时间父亲很焦虑,心里很沉重,国民党实力不济,共产党节节胜利。1948年,我在南京的秣陵路小学读三年级,我们住的是父亲工作单位的宿舍,是个好大的四方院子,有很多天井祠堂,我们就住在里头,冬天冷得要死,手上生冻疮。期末考的时候,墨水都凝起来了,笔写不出字来。
外婆和舅舅回了宜兴老家,不跟我们在一起了。我们一家人又开始逃难了,躲避内战。爸爸以为这次还像抗战一样,西南可以保住,就带着我们跑到了贵阳。没想到他想错了,到了贵阳不久,国民党被共产党打得一直后退,我们马上又跑去了广州。1949年初我们到了广州,在旅馆里住了三个月,然后4月4号到达台湾基隆。到了台湾又感到台湾不保,全家又跑到了香港。
在贵阳,爸爸在家的时候帮我补习,我考取了一个只取两名的好学校的插班,结果一天没读就走了。到了台湾我在国语实小插班,但因为失学太多,我语文、算术都跟不上,后来父亲说要去香港我高兴死了,因为可以不上学了。
我们在香港过得很糟糕。父亲失业,没人找他写文章,而且香港都讲粤语,我们一句广东话都不会讲,被欺负,他们非常排斥我们。我们住在一个小岛上,叫鸭脷洲,岛上都是渔民。我们住在三层楼,没有水,要到楼下的街上接水,我每次排队前面全是插队的,我永远拿不到水。
我们在香港住了半年,朝鲜战争爆发了,美国派来了第七舰队,台湾的局势稳定下来了。父亲被台湾《中华日报》邀请回台湾写社论,我们全家才再次搬到台湾,真正安定了下来。我先在台北上福星小学五年级,然后全家搬到了新店,新店就是我最后的老家了,在这里住到我出国。
三
我家住在新店的碧潭,是台北郊区的一个风景区。这里有个很漂亮的小吊桥,是模仿旧金山的金门大桥造的,还有一个悬崖,对面是文山,是产茶叶的地方。
我从新店国小毕业,本来考取了台北第二女子中学,它在台湾最大的飞机场——松山机场附近,父亲怕松山机场会遭到轰炸,而且从新店到二女中又很远,要转两次车,每天上学单程就要一个多钟头,所以不同意我去上学,于是我就去了当地的文山中学读书。
文山中学学生不太读书,又顽皮,但这个学校以游泳和篮球闻名,上体育课时老师就带我们到碧潭游泳,叫你自己去游,现在想想真的是很危险。我从小就喜欢读书,所以没有受太大影响,考试总是前几名。初中毕业后,我考上了台北第一女子中学,是台湾最好的重点中学。当时大学太少了,考大学压力很大,大家一天到晚都在读书考试,两天一小考三天一大考,那三年大家都埋头读书,不顾一切。北一女管得很严,一定要穿制服,头发要剪到齐耳。我们还有军训课,打过靶,我的子弹都不知道飞到哪去了,因为我不会闭左眼瞄准。现在想起来真是好玩。
1958年我考进了台湾大学农业化学系。进台大后就很自由了,上不上课没人管,想穿什么随你便,反正到时候能毕业就行。我是1962年毕业的,那时候是一阵风,大家都要出国,可能是因为台湾太小了,没什么出路,反正从比我们高几届的开始,一直到1980年代都是这样。我哥哥出国了,我也出国了,然后弟弟妹妹姐姐都到美国来了。
我先生张绍进是江苏涟水人,就是现在的淮安市。他的家庭背景跟我是非常像的,但他青年时期的经历比我还要戏剧化。他的祖父是务农的,一定要让儿子去读书,他父亲叫张迺藩,很争气,考上了北京大学。后因加入了国民党,就转学到南京去上中央大学,1930年从中央大学毕业。他跟陈立夫、陈果夫非常熟,跟我父亲也认识。
1933年,张迺藩被任命为江苏宿迁县长。抗战初期,国民政府想以上海这个国际都市作为抗日战场,引起世界各国的注意,就把上海附近的年轻县长都调过来,张迺藩被任命为太仓县长。淞沪会战时,他跟着国军共进退,帮国军挖战壕、造工事。上海沦陷了,他几乎被日本人抓到,非常曲折地跑到苏州,跟着军队撤退,最后到了重庆,在蒋介石侍从室第三处做事,相当于陈果夫手下。
他们家一共四个男孩,二哥抗战时期在重庆得脑膜炎去世了;大哥张绍远和三哥张绍迁,都在台湾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并来美深造,在美国成家立业,事业有成。大哥已经去世了。
绍进比我大三岁,他出生于1937年,对抗战的记忆比我清楚。他说在他一二年级的时候,在重庆有一天他的老师讲起南京大屠杀,从南京逃出来的人也讲,报纸上也刊登了,当时说被屠杀的人数是35万,而且讲到了日本人如何在南京烧杀掠夺,惨绝人寰!
抗战胜利后,他们一家去了南京。内战开始后,他父亲很晚才决定要离开,先跟他大哥去了台湾,留下了母亲、三哥还有他三个人。他母亲很聪明,用了计策,先到了香港,1951年才到台湾的。他到台湾的故事很曲折,无法在此一一叙述。
他到了台湾后也住在新店,就进了文山中学,跟我哥哥同班。他的数学非常好,老师在上面讲,他在下面做自己的习题,一抬头发现老师讲错了,就问那个老师这是怎么回事,结果把老师“挂黑板”。我哥哥回家后说,张绍进今天把老师弄哭了,于是我就听说了这个“怪人”。哥哥跟他成为好朋友后他常到我们家来玩,哥哥很钦佩他,不会的数学题、物理题都去问他。
他们考大学的那一年是几个学校联考,数学题特别难,很多人都考不上六十分,但他考了九十几分,虽然他国文不行,但还是考上了甲组也就是数理化组的第一名,上了台湾大学。大家都很诧异,怎么会冒出一个文山中学的状元来。这是破天荒的事情,记者跑到他家访问,报纸都刊登了,县长还来给他颁奖,文山中学放鞭炮庆祝。
哥哥在我面前讲了很多关于他的事,他从来不跟女生讲话,不敢跟女生接触,如果不小心碰到了还要吹一吹,太好笑了。不过后来我们在大学见面,他就“正常”了,敢跟女孩子讲话了。我上了台大,他在新竹清华大学读研究生,我们开始约会。那时候台湾很稳定,也很自由。好莱坞的电影影响力很大,奥黛丽·赫本的《罗马假日》,一下子全台湾轰动,每个人的头发都变成了赫本头,衣服也都是电影里的款式。那个时候的电影我们都去电影院看过。
绍进高我三届,他在清华大学读了两年硕士,又服了兵役,所以1962年的时候,正好跟我一起申请去美国读书。他申请到了哈佛大学物理系,我申请到了哈佛大学生物化学系,就这样一起去了美国。
四
到美国两年以后,1964年8月29号,我们结婚了,在哈佛大学的纪念教堂办的婚礼,到今年已经是60年了。那时候我们很穷,也不知道提前一年就要预约教堂,人家结婚多半是在下午,那天教堂唯一有空位的时间是早上九点,于是我们就是早上九点办的婚礼。参加者都抱怨太早了,起不来。婚礼很简单,我哥哥在伯克利大学读博士,他也是靠奖学金过活,他一路搭车过来,很辛苦,婚礼上他代表爸妈把我交给绍进,我的博士论文指导教授主持婚礼。
那个时候,我们俩每人每年只有3000块美金的奖学金,学费就要1500块,只剩下1500块生活费,所以我们很节省。婚后我们住进哈佛大学结婚学生宿舍,租金很低,但宿舍是在剑桥校园,而我的课在波士顿市区的哈佛医学院。为了我每天去实验室方便,后来我们租了在波士顿离哈佛大学医学院很近的一个小公寓,一直住到博士毕业。
毕业后,我去了普林斯顿大学生物系做博士后。绍进去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这个研究院是独立于普林斯顿大学的,爱因斯坦当年就在这里做研究。这个机构没有学生,只有研究员,非常纯粹的理论研究机构。绍进研究的是高能核子理论物理。
在普林斯顿待了没几个月,我就怀孕了。那时候我做有关slime mold(黏液菌)的试验有一个重大突破,于是我拼命在产前把试验结果做出来并且后来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
1968年3月28号,纯如出生了,生产过程很顺利。但是我们两个人没有经验,我就捧着育儿书看,紧张得不得了。我是研究科学的,纯如每次只吃一点点奶,我很着急,不知道她吃饱了没有,就记录奶瓶上的刻度,计算她每天到底吃了多少,周围人都笑死我了。
她爸爸说,她不吃就表示不饿,不饿就不让她吃,但是她一哭,我就忍不住赶快去喂,一天喂十几次,每次她只吃一点点,还一直哭,我心里痛得不得了。后来她爸说我来管,他一天就把她治好了,不是每个小时都去喂了。当时闹了很多笑话。
1969年,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分校给了绍进一个助理教授的职位,那年夏天,我们就搬到了厄巴纳,在那里住了30多年。
纯如小时候我没觉得她有什么特别,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她是有点与众不同。纯如非常敏感,人家推她一下、揪她一把,对于她来说都是天大的事情,她会回来跟我报告。
三岁的张纯如
绍进第二次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做研究的时候,那是1972年,纯如四岁。在普林斯顿幼儿园,纯如很害羞,见到陌生人不肯讲话。老师特别好,发现她喜欢看书,就鼓励她把读到的故事讲出来,后来她居然说自己也要写书。家里有很多电脑打印的废纸,背面好好的,我就拿来给她画画,她要写故事,但是还不会写字,我就让她画出来,然后让她把故事讲出来,我来帮她写,她说什么我写什么,然后把纸订起来,就变成一本书了。纯如鼓起勇气拿给老师看,老师说这个好,让她在全班面前念出来,是关于官兵捉强盗的故事——这是她“写”的第一本书。
后来她在小学一年级时,老师说她在班上一句话不讲,但是她一回家就完全释放出来,讲个不停。为了让她在外面多讲话,我们请她朋友来家里玩。有个小男孩跟我们住在一条街上,他们俩关系很好,放学一起走路回家。男孩的妈妈就跟我说,Iris好会讲话,他们一起在路上走,她儿子说都是Iris在讲话,他插不上嘴,所以我就知道她没有问题。
纯恺是1970年出生的。我们有意让他们姐弟在家里讲中文,在外面讲英文,结果他俩一天到晚讲英文,不讲中文,我们也没办法。有时我用中文问她听不听得懂,她说当然听得懂,尤其你骂我的时候特别听得懂。
纯如有一次非要去测自己的IQ,我说你测IQ干什么,一个人的成功是靠自己努力得来的,即使IQ很高,自己不努力,也做不了大事。但是她非要测,结果测出来IQ很高,但是我一直提醒她,后天的努力才是最重要的。
九岁的张纯如
纯如的观察力很好,注重细节,经常会提出令人深思的问题。绍进有一次从台湾带了蚕卵回来,蚕宝宝孵出来后,每天采桑叶喂它们,全家开始养蚕。纯如为养蚕还写了诗,做了报告。她的数学很不错,她不会的时候就问爸爸,高中的时候数学比赛还拿过奖。她的逻辑也很好,思维很快,我是辩论不过她的。她也喜欢音乐,小时候学过钢琴,一直到高中。她还很喜欢唱歌,大学时还专门去音乐系学声乐。
纯如特别喜欢看书,看书速度很快。我们每个礼拜带她和弟弟去图书馆,每次她都选十几本书回来,越看越深,看莎士比亚这些世界名著,我跟她在英文、文学上的差距越来越大。她写诗,我帮她打出来,结果同学说是Iris的妈妈帮她写的,她回来告诉我说别人不信是她写的,我说你不要在意,我是写不出诗来的。
张纯如、张纯恺与母亲张盈盈
申请大学的时候我们什么都没有管。我和她爸爸都是在哈佛拿到博士的,纯如也想去哈佛,我想小孩还是会在无形中受到来自父母的压力,因为我们什么也没说,没说她一定要上常春藤名校。如果我们不是哈佛的,她就不会一定要去哈佛。但我们知道她的成绩肯定进不了,她就读的伊利诺伊大学附中都是教授的小孩,都是高材生,她在50人里排名中等,肯定申请不到常春藤名校。我心里很明白,她心里也有点明白,但既然她要申请,我们就心照不宣,默不作声。
纯如从小就很要强,但是她不为了分数而读书,喜欢的课程她就考得很好,不喜欢的就不去读,所以她的排名不是那么高。申请一所学校就要交一笔钱,还蛮多的,我说你要申请多少就去申请多少,反正我给你交钱就是了。所有的申请都是她自己填的。
后来纯如申请到了康奈尔大学,也是常春藤名校,她兴冲冲跑过来跟我讲。她还申请到了芝加哥大学和伯克利大学,她想去芝大,但是芝加哥的环境太坏,我们劝她伊利诺伊大学一点也不比康奈尔大学或芝加哥大学差,你爸爸在这里教书,回家吃饭也很方便,她就选择了伊利诺伊。
纯如高中的时候,我们有一次回台湾,花了100美金买了一台电脑,比美国便宜很多。绍进跟他们姐弟说,将来一定是电脑的时代了,绍进很早就开始用email,一到星期天就把两个小孩带到computer lab里头,让他们去玩。他们高兴得不得了,玩了很多computer game。而且当时伊利诺伊是美国五大电脑发展中心之一,计算机系在全国排名是很靠前的,所以纯如就选择了计算机系。
在伊大附中的时候,纯如想进入伊大学校里的计算机俱乐部,进这个俱乐部按规则需要通过一个考试,纯如考过了,结果那些人一看是个女的——这个俱乐部全是男的,没有女的——不想要她,就说这个考试不算,要她再考一次。纯如气死了,考过了你们还要修改规则,简直没有道理,一气之下就不要参加了。
纯如在高中的时候数学很好,到大学学习高等数学,她就不大有兴趣了,不愿意花时间去学。同时她也选了很多文学方面的课,文学系的老师都很喜欢她,那么她就想转系了。考虑到就业等问题,她决定转到新闻系,而且那时候她已经开始写文章了,发表在学校的报纸上,转到新闻系非常顺理成章。
五
纯如九岁十岁的时候,她问我们以前在中国做什么,为什么会来到美国。我对她说我们在你这个年纪都在逃难,还讲了我父亲从南京逃出来跟母亲在芜湖会合的故事,当然也讲到南京大屠杀了。我的父母来厄巴纳一起住的时候,也会给她讲一些故事。她是一个很好奇的小孩,听到我们这样讲,就去图书馆找资料,结果什么都没找到。在美国普通的公共图书馆,当然找不到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内容。她去问老师,老师也说从来没听说过这件事。其实纯如很早的时候就埋下了写作南京大屠杀的种子。
大学毕业后她在几家报社工作,后来决定当一名作家。她一直在寻找写作题材,脑筋很快,写字也飞快,总是带着纸笔在身上,想到什么就马上写下来,而且一本书只写到一半,就开始想下一个选题。她写下了几百个题材,字写得有的时候我都看不懂。纯如经常跟我聊她的想法,我有时候跟她说这些都是美国人会写的东西,你既会中文又会英文,可以写写中国的故事。你那么喜欢《飘》,其实这种故事在中国特别多,比如杜立特行动、比如南京大屠杀。
她的第一本书是钱学森传记。1994年12月13号,纯如刚刚完成这本传记的写作,去加州库比蒂诺参加了一个侵华日军暴行的会议,会议上展出的照片让她下定决心写作南京大屠杀。图片展是湾区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举办的,纯如在会议上碰到史维会发言人丁元,丁元一看以为她是个学生,要写一篇读书报告,结果纯如一本正经地告诉他,我是一个作家,已经要出第一本书了。丁元和许多史维会成员都非常热情,给她介绍了很多日本侵华历史这方面的研究者。
史维会介绍在华盛顿特区的李圣炎给纯如,他让纯如住在他家里,还开车接送纯如到火车站搭车去美国国家档案馆查资料,对她非常好。史维会的研究者、这些业余历史学家对大屠杀是很有研究的,他们都在帮助纯如。专业历史学家里面,像吴天威和朱永德也在帮助她。
大屠杀中的掠夺、烧杀、强奸,这些案件几乎都是一样的,看到后来纯如已经麻木了,她都不知道该怎么动笔写了。写完初稿,她拿给我看,我觉得不行,她的编辑苏珊·拉宾娜(Susan Rabiner)也觉得不行,纯如有点失去信心了。苏珊是犹太人,她非常了解纳粹的大屠杀,她们就商量怎么完善初稿。那几个月,纯如大概不睡觉了,很紧张,一直在修改书稿。她修改得很快,改好了拿给我看,我觉得改得已经很好了,比第一版好很多了。书的视野很大,不只是针对日本人,她写的是人性的黑暗,是极权的可怕。
《南京浩劫》英文版封面
《南京浩劫》出版之后大火特火,这是谁也没有料到的。纯如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我当时只是希望这本书能放在书架上,有人看到就很好了。纯如的知名度一下就变得特别高,人也变得特别忙。我想第一她很年轻,第二她特别会讲话,临场反应非常快,又很会辩论,不管人家问她什么问题,她都能侃侃而谈,而且有理有据,所以特别受媒体追捧。
一下子太火了,结果就有很多历史学家对她不满,挑她的错。我相信这里面一定有嫉妒的成分,人家研究一辈子都出不了名,你小毛头才出了一本书就这么有名。日本人当然恨死她了,他们用了很多办法去抹黑她。纯如书里把日本人的名字搞错了,他们就说她根本不懂日文,由此想把整本书都推翻掉。
其实书刚出来的时候,大家一片赞誉,直到登上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榜,才引起日本右翼的攻击。对于受到的攻击,纯如一直不肯跟我们讲,我们直到2003年搬到加利福尼亚才知道一些,她收到子弹信件已经是很后面的事情了。她的先生也讲,他们其实没有受到过什么人身攻击。
之后纯如参加了很多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讨论和会议,她对索赔的事情尤其关心,也一直觉得南京大屠杀不是侵华日军唯一的罪行。慰安妇和731部队的事情她也很关心。
有人问我:纯如一生的贡献是什么?我认为纯如除了出版《南京浩劫》一书外,最重要的是找到了拉贝日记。约翰·拉贝当时在南京以第三者的身份见证了南京大屠杀,他忠实地记载了1937年在南京发生的事情,日本没法狡辩说南京大屠杀不存在。
纯如和人权律师巴里·费舍尔(Barry A. Fisher)写过好几篇文章批评美国政府放弃了日本应对二战中美国军人的赔偿,谴责美国政府拒绝在法庭上对二战劳工和慰安妇伸张正义。另外,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纯如为美国少数穆斯林族裔被歧视、被当成攻击对象而发言,维护人权。所以张纯如不只是为华人伸张正义,或只是为亚洲人伸张正义,她是为全人类伸张正义。她是一个人道主义者。
1998年,张纯如与张盈盈
六
纯如写完《南京浩劫》之后就专心写作《美国华人》了,她在《南京浩劫》发表之后,就选定这个主题了。2003年,硬皮新书一出版,纯如开始为《美国华人》做宣传推广,全美国巡回演讲。一年之后,软皮版出版,又要叫她全美巡回演讲签书。出版商太贪心了,日程排得太紧凑,一两天一个城市,完全不顾纯如的身体,纯如人太好了,她没有拒绝。但新书宣传活动上,大家对她提问最多的还是南京大屠杀的问题。
《美国华人》英文版封面
2004年5月份回到家的时候,纯如的先生就发现她完全不一样了。她特别累,而且觉得有人威胁她。在一次活动上,有个人对她说:“如果你加入我们的组织的话,或许可以安全些。”这件事情有没有真的发生,我们到现在都不知道,我们也不愿意逼问她到底怎么回事。
纯如和她丈夫很难怀孕,2002年他们通过代孕有了儿子Christopher,很不容易。新书推广活动回来,纯如想专心照顾Christopher,她发现他不太跟别的小孩子玩,怀疑他有自闭症。那时候Christopher还不到两岁,我们真的是没有看出来什么,纯如就说他有问题,然后拼命地研究,在网上找资料,找医生咨询,完全把它当成一个课题,心力憔悴,人很消沉。这对她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另一方面,纯如还要写自己的第四本书,她想写菲律宾的美国战俘。为这本书她正在收集资料,采访了几个老兵,大概进行了10%,这些访谈资料现在还存在胡佛研究所里。这些老兵的经历非常惨,这当然也是对她的精神状态不好。
8月,纯如决定去路易斯维尔采访一个坦克营的老兵。出发之前她已经不对劲了,到了旅馆她既没有睡好,也没有吃饭,又觉得有人要害她——电视里播放的影片她觉得是有人故意吓她的。纯如崩溃了。人家把她送到医院,我们马上飞过去照顾她。
从路易斯维尔回来,纯如看了几位精神科医生,医生开的药太重了,纯如不想吃,自己停掉了。后来我还特意去咨询哈佛大学的精神科医生,他说吃这种药自杀的人好多,但是这些案件都是不能公开的。有一个患者吃了一段时间药,以为自己好了,没想到几个月以后他还是自杀了——停药后的几天一直到3个月都是危险期,药要慢慢戒掉,不能一下子停掉,刚停药的时候是最危险的时候。
我一直觉得,研究南京大屠杀当然对她的精神没有好处,她看了那么多血腥的东西,但这不是纯如自杀的直接原因。她去世离这本书出版已经过去了7年,她都预计写第四本书了。我觉得新书的巡回演讲对她不是很好,太累了,又发现小孩是自闭症,很多事情连起来,最后精神药物的副作用导致了这个悲剧。她从前最不能想象有人会自杀,结果自己走上了这条路。
2004年11月9号那天早上,他先生发现纯如半夜开车出走了,而且留下遗书。我们开车出去找她,到处找都找不到她,把我们急死了。其实9号的清晨警察就发现她去世了,一直没有公布,调查后才通知了她的先生,然后她先生才来告诉我们。我跟绍进觉得天旋地转,好像跌入一个黑洞里头。纯恺正在纽约出差,他听到消息大哭。绍进从来不哭的,那天他也没哭,但是过了几天后他突然嚎啕大哭。我一直没有哭,我觉得自己的眼泪在那段日子已经流干了。
我们是2002年11月从伊利诺伊州搬来加利福尼亚州的,对加州的环境还不是很熟悉,朋友也不太多。我打电话给丁元,他难过得不得了。纯如最后几个月的情况,她不让跟别人讲,我怕我们讲出去会让她觉得我们背叛了她,所以大家都不知道,连我的兄弟姐妹,她的表兄弟姐妹都不知道。这么受欢迎的一个人,这么有活力的一个人,这么热情的一个人……对家里所有人来说都是个非常大的打击。
葬礼全部是以丁元为首的史维会包办的。他们帮忙选择墓地,提前通知警察维护秩序,还去租了200个椅子放在墓园小教堂前面的草地上。我心里想,哪会有那么多人来,你租那么多椅子放外头干吗?葬礼的教堂只能容纳100人,外面放了200个椅子,结果现场来了500-600人,很多人从外地飞过来,现场需要警察维持秩序,葬礼上帮她抬棺的都是她的表兄弟。丁元的预判完全正确。
张纯如墓
七
纯如纯恺姐弟俩感情很好,纯恺受到了很大影响。那段时间他每天都来看我们,我一直在扪心自问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反省自己要是怎样怎样就好了,一直持续了几个月。儿子说如果你还是这样一天到晚提这个事情,我就不再来了,他下定决心不再这样下去了,他是为我好,早点走出阴影。
2006年,我跟绍进才逐渐开始走出家门。看到那么多人对纯如那么爱,那么怀念,让我们感到安慰,也给了我很大的力量。我们收到了很多卡片、慰问信。史维会组织了追悼会。有人组织买纯如的书捐给图书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要给纯如立一个雕像……我觉得那么多的人对她都这么好,我也要有勇气站起来。
张纯如雕像
2006年3月28号,这天是纯如的生日,史维会帮我们成立张纯如纪念基金会,我要继续纯如的事业。先组织了征文比赛,第一年的题目是“张纯如的书对你的影响”,第二年的题目是“否认南京大屠杀的代价”,得奖的文章把它们印出来出版。我们加入了史维会,跟他们一起开会,做一点教育工作。史维会还资助对抗战有兴趣的高中老师和学者,让他们暑假到中国去考察日军侵华遗址,如卢沟桥抗日战争纪念馆、上海的慰安所遗址,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云南腾冲远征军陵园等。就这样慢慢让自己忙碌起来,为她而活,渐渐走出来了。现在我们老了,八十岁以上的人了,实际工作我们都没办法做了,只能出出主意而已了。希望下一代能接棒,可是下一代人毕竟没有像我们这一代亲身经历过,终究隔了一层。很难。
记得2005年,日本想要加入联合国常任理事会,正好那时候纯如去世不久,史维会的丁元和李兢芬组织大家在网站上联合签名抗议反对,当时还有国内的918爱国网一起发动签名。报纸上好多文章都提到张纯如揭露了南京大屠杀,日本连南京大屠杀都不承认,怎么有资格入常呢?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在一篇文章里提到,来纪念馆的外国人,几乎人手一本纯如的书,他说这本书影响力好大,在世界掀起一阵热潮。
纯如的一本书,引起了很大“涟漪效应”,好像一个石头丢到湖里,一圈一圈的水纹向外扩散。自从纯如的书出来之后,不少西方学者开始研究东方战场了。如牛津大学教授拉纳·米特(Rana Mitter)写过一本《Forgotten Ally: China’s World War II, 1937-1945》(《中国,被遗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战争全史》),还有李培德教授是后来史维会的会长,他本来是研究文学的,由于被纯如的演讲打动,开始研究抗战,他编辑了一本很重要的书——叫Japan War Crime(《日本战争罪行》)。国内也开始系统化地研究南京大屠杀,上百册的抗战历史集出版、后来还有731部队、慰安妇,东京审判……还有很多其他书籍出版,如小说类,比如哈金写了一本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小说《南京安魂曲》。舞剧方面,如佟睿睿导演的舞剧《记忆深处》,以张纯如、魏特琳、拉贝、东史郎为主要人物,非常震撼。
2007年南京大屠杀70周年,加拿大史维会还拍了电影《Iris Chang:The Rape of Nanking》,郑启蕙演张纯如。著名导演比尔·古顿塔格(Bill Guttentag)受富豪泰得·里昂塞斯(Ted Leonsis)资助,拍摄了纪录片《南京》。里昂塞斯看了纯如的书后大为感动,出资一百万元聘请古顿塔格拍摄的。两个影片在北美和中国都得到好评,对大众的南京大屠杀历史教育有很大的贡献!
我对女儿的英文回忆录《张纯如:无法忘却历史的女子》是2011年出版的,是描述纯如一生的事迹。中文简体、繁体翻译我的回忆录于2012年同时出版。我花了七年的时间把纯如给我和她爸爸的信件和她的演讲稿整理出来,给大家一个真实的张纯如。
《张纯如:无法忘却历史的女子》中文版封面
2017年纯如祖父的故乡淮安建立了张纯如纪念馆,收集了纯如遗物,展示了她一生的事迹和精神,纯如一定会很安慰能在这美丽的古淮河边安息!
张纯如纪念馆
2019年美国加州圣荷西市在纯如最后住宅附近的公园命名为张纯如公园,公园的主题是她的信仰:power of one——一个人的力量。公园里有一艺术设计是象征她对世界的影响:所谓的“涟漪效应”,就是公园中间有一处五个同心圆的小山丘,在最上面有一个很大的锥形石头。这就像一块石头扔在水塘里,会产生一圈圈的涟漪,寓意一个人的力量可以影响社会甚至整个世界!
张纯如公园
公园主题:power of one
公园里介绍张纯如生平碑
八
《南京浩劫》日文版的出版过程非常复杂,搞来搞去,在纯如生前也没有出出来,直到十年之后,2007年才出版。很多人说是纯如不让他们修改,其实是日本出版社不仅要改原文,还要加注释,比如七七事变,他们要加一个注释说是中国人先挑衅的,简直是在开玩笑,怎么可以这样注释?纯如不同意,他们又说另外出一本书,叫“如何解读《南京浩劫》”, 跟她的书订在一起。这个也非常过分,纯如说要出你们自己出,不要跟我的书订在一起。当然,出版社受到了好大压力,据说收到了死亡威胁,参与的人很多都退出了,他们也要想办法自保。十年以后,另一个出版社接手,而且找了一位在日本的中国人翻译的,没有改动一个字。十年之后才有日文版,可能日本已经觉得无所谓了,想出就出吧,有人要看也可以去看。出版后销路当然不广,也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
纯如的《南京浩劫》这本书刚出版时,受到许多的历史学家的推荐和称赞。北美主流媒体一片叫好,上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榜。因此纯如出了名,这引起了日本右翼的恐慌。他们想尽办法来抹黑纯如。有人批评她是个记者,不是历史学家,不是专业的。不是专业人士也可以做研究呀!不能因为不是历史学家写出来的历史就不靠谱。
纯如去世后,我觉得日本对她的抹黑更变本加厉了,好像下了定论,这本书根本不值一提。但是想把它压下来没那么容易。我很感谢兰迪·霍普金斯(Randy Hopkins),他是法庭辩护律师,也是业余历史学家,他看到自己很喜欢的一位历史学家阿尔文·库克斯(Alvin Coox)在《日本回声》上的一篇文章,跟他之前的写作风格完全不一样,觉得有点奇怪,怀疑是有人代笔。这引起了他的兴趣,就去研究《日本回声》这本杂志,这样才揭露出日本外务省赞助一些学者对纯如的打压。
兰迪花了一年的时间研究《日本回声》这本杂志里批评纯如的文章,他写了一篇46页的论文,名为《南京回声》,为纯如打抱不平。这篇文章中他举例批评纯如最多的傅佛果(Joshua Fogel)教授。我很早就知道他,他写了很多骂纯如的文章。傅佛果骂纯如后来变成人身攻击,非常缺乏研究学者应有的风度。兰迪在他的《南京回声》里举出了许多例子,来展示傅佛果批评纯如很多是自相矛盾,没有道理。我非常感谢孙远帆和程以克两位翻译者,义务把兰迪的论文翻译成中文,很高兴能发表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杂志《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这篇论文很长,有兴趣的可以自己去看看。
这篇论文还谈到一位日本历史学家叫秦郁彦。在纯如《南京浩劫》刚出版时,在普林斯顿大学研究会上,纯如曾经反驳他说的南京大屠杀死亡人数。后来秦郁彦在一篇文章里故意把纯如说成是一个女权主义者,说他在会议上本来有很多问题要问她,但是我不敢,因为如果我讲错话,人家还以为我是性骚扰,怕被告——他就是讲这种莫名其妙的话转移主题。秦郁彦说大屠杀的人数不对,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对,纯如讲的不对,别人讲的也不对。什么他都说不对,但是他自己又讲不出什么是对的,最后自己也没有结论。
兰迪的这篇文章《南京回声》最重要的是发现抹黑纯如背后的是日本外务省,他们出钱支持发行这本伪装杂志《日本回声》邀请“学者”来抹黑纯如,而且是用英文发表,印了几十万册专门向北美地区分发。如果我们还相信只是日本右翼分子否认南京大屠杀,那只是安慰自己。不肯承认战争罪行的是日本政府一贯的政策和态度。这就是目前在纯如逝世20年后,日本不但没有反省在二战中对中国、对东南亚地区的战争罪行,反而变本加厉想要恢复军国主义,继续想做它的“大东亚共荣圈”的白日梦!
纯如写作《南京浩劫》是希望从历史中吸取教训,这种反人类的暴行不再发生,以达到世界和平的境界。但是目前世界各处仍是战事连连,其实我心情非常的沉重。我希望年轻人能拿出勇气,接下纯如的火炬,真正为人类和平继续努力奋斗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