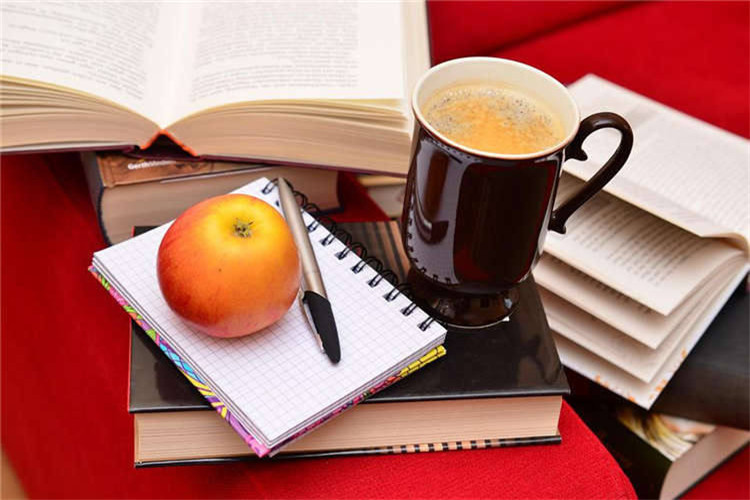巴金诞辰120年|巴金如何谈论自己的作品?
尽管西方文论中早有“作者已死”的论调,突出读者在作品价值和意义生成上的主要地位。但作家如何看待自己的文字,作家写作过程中有哪些心理活动,一些人物是否有典型、是否有现实依据,始终是读者心中十分好奇的问题。巴金就是这样一个不吝于谈论自己对作品的理解、甚至对于其中部分人物好恶的作家,他曾在自己的小说《萌芽》的题记中写道:“对于自己的文章总不免有点偏爱,每次在一本书出版时我总爱写一些自己解释的话。”他一生写作了大量自己作品的序文、评论,有时甚至同一本小说要写作十篇以上各类序文、后记,阅读这些序文,可以窥见他的个性和喜好,有时也能看到历史沧桑变化的痕迹。
巴金(1904年11月25日-2005年10月17日),1980年摄于上海
巴金如何评价他的小说?
巴金在序跋中常常坦诚地流露对自己作品的爱,这种情感使他的创作激情与个人生命体验紧密交织。“我的写作就是我的生活。”他对《爱情的三部曲》——《雾》《雨》《电》——有独特的偏爱,曾说在这三部小说中“有我喜欢的东西”(尽管之后他的态度又有变化),坦言:“我从来不曾把我这个‘灵魂的一隅’打开给我的读者们看过,因为我觉得这完全是个人的事情。”《爱情的三部曲》是具有“私人性质”的作品,“咽在肚里的自己的话却成了火种,在我的心里燃烧起来”。这三部作品是激情之作,通过其中的人物表达了他对爱情、理想与自由的追求,也反映了他的社会反思与热情。《家》是他另一部有着深厚的情感联系的作品,他坦言:“我的确喜欢这本书。小说里并没有我自己,但是我在这里看见了我的童年和少年。”(《家》五版序,1936年)他将作品与自己的经验融合,尤其是觉慧这个角色,寄托了他对于自由和反抗的渴望:“觉慧不是一个英雄,他很幼稚。然而看见他,我就想起丹东的话:‘大胆,大胆,永远大胆!’我应该拿这句话来勉励自己。”(《家》五版序,1936年)
《爱情的三部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6月版
他也毫不讳言对部分作品的失望与不满。在《火》的序中,他坦诚提到对这部作品的遗憾:“我写这小说,不仅想发散我的热情,宣泄我的悲愤,并且想鼓舞别人的勇气,巩固别人的信仰……但是看看写完的十八章,自己也觉得这工作失败了。”(《火》第一部后记,1940年)他在写作中缺乏充足的时间和经验,导致作品未能如愿传达他想要的思想与情感。类似这样的描述,在他的序跋中非常多见,他对自己大多数的创作都抱有类似的态度,认为是“失败之作”,并且没有一部满意的作品。
在序跋中,巴金还会直接表露对于部分人物的爱憎之情,这在一些秉持着写作需要更客观的视角的评论家而言,可以说是很罕见的姿态。他喜爱那些勇敢反抗、不屈服于命运的人物,例如《家》中的觉慧,那个“幼稚而大胆的叛徒”,寄托了巴金对于自由与变革的希望。而对于觉新这样的角色,巴金的态度则更为复杂。觉新象征了对封建制度的屈服与妥协,“他(陈剑云)甚至比觉新还更软弱,还更缺乏果断”,觉新是他口中软弱的代言。他在序跋中传达出对软弱者的理解与批判,但也显露出一种无法抑制的怅惘。
巴金敬重那些为自由而抗争的灵魂,喜爱他们的勇敢和坚持,同时,他对那些屈服于命运、没有勇气去抗争的人物充满复杂的感情,既有理解,又有遗憾。一个爱憎分明而又热情洋溢的创作者的形象通过序跋呈现在了读者眼前。阅读巴金的序跋,就像是在和他对话,感受他的情感、个性。
巴金的序跋有什么特点?
巴金的序跋不仅是作品的附加说明,更是他表达个人思想、情感和艺术观念的重要途径。在这些序跋中,他不断与读者、评论家对话,显示着他对于小说艺术的理解。有时序本身也成为他文体实践的场所,他在序中探索不同的形式风格。
在序跋中,巴金特别喜欢探讨作品的真实性,回应读者对其作品是否来源于生活的好奇。例如,在《家》的序言中,他提到:“有不少的人以为这是我底自传,其实,这是一个错误。”他常常作此类申辩,有时甚至长篇大论。但同时,巴金又在许多地方不断地表示自己某些小说失败的原因是“没有生活”,又说“我的创作就是我的生活”。这看似有些矛盾的表述其实体现了巴金对于创作与现实关系的深思,以及他对虚构文学如何构建真实感的理解。他希望通过觉慧的故事,让读者看到一个青年在封建家庭中的挣扎和觉醒。对巴金来说,创作的核心不在于简单复制生活,而是通过虚构揭示更深层次的社会现实。
序跋中充满了巴金的热忱,语言中洋溢着对理想和人性的热爱。尤其是他与刘西渭围绕《爱情的三部曲》的通信中,刘西渭强调巴金的“热情”,甚至称其为“幸福的巴金”,但巴金却显露出了不同的意见,对他而言,“信仰给热情开通了一条路,让它缓缓地流去,不会堵塞,也不会泛滥”。是信念贯穿了他的创作,而不仅仅是热情,使得这些作品充满了生命的热度和对社会理想的不懈追求。他用直率且热烈的语调谈论爱、理想和青年人的命运。这种解释并非仅为澄清读者的疑惑,而更像是一种信仰的宣言。
体裁上的独特性也使得这些序跋颇具文学魅力。有时,巴金喜欢将序写成一封书信,使得序跋带有明显而独特的私人性质,诸如《家》的第一版序。而在更多的序文里,巴金有意以《野草》式的散文诗般而又抽象的言辞,使序跋本身成为作品文学性的一个部分。这在《复仇》的序和《最后的审判(代跋)》中体现得格外明显,我将《最后的审判(代跋)》的结尾部分附在这里,可以感受这种独特文体的魅力:
我醒过来的时候,挺直地躺在床上,薄薄的被盖着我底身子。四围没有人声,屋里抖着熹微的晨光。我底心还在胸膛里跳,我底身子还有热气,我底手还能够动,我底口还能够发声。我很快活,我知道我还没有死,我还活在这世界上。……
渐渐周围起了人声。
这不复是黑夜。天已经亮了。
藏在序文里的时代印记
巴金在《家》的序文与后记中,对这部小说的主题和反封建的定位表现出显著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反映了他个人思想的不断深化,也与不同时代的社会与文化氛围息息相关,尤其是在“文革”后的“新时期”对“文革”的重新定位中,巴金对封建主题的理解逐渐走向复杂化与深刻化。
《巴金选集1·家》,四川文艺出版社,2015年6月版
在1930年代的序文与后记中,巴金对封建制度的控诉直接而激烈。他明确表示,《家》的创作动机在于反对封建制度,反对压迫个体生命的旧礼教。正如他在1937年的《十版代序》中所说:“我所憎恨的并不是个人,而是制度。”这种愤怒在《家》中通过对高家这个典型封建家庭的描绘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巴金通过塑造觉新、觉民、觉慧三兄弟的不同命运,展现了青年在封建家庭中的不同应对方式,尤其是觉新的软弱和屈从成为封建礼教压迫下的悲剧典型。他希望通过这些角色,唤醒人们对封建制度的认知与反抗,尤其是对青年自由与尊严的渴望。
随着时间的推移,巴金对《家》反封建主题的理解开始发生变化。1953年新版后记中,巴金依然重申了反封建的立场,但他对自己的创作进行了更为冷静的反思。他坦诚地承认,自己在创作中“太重视个人的爱憎”,缺乏冷静的思考和对社会问题建设性解决方案的提出,“指出一条路”。同时,他也提出“《家》已经尽了它的历史任务了”,在写文章时的1953年,“路”的含义十分明确的,那时的知识分子们真诚地相信封建制度已经彻底被消灭了,我们正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而在1977、1978这两年间,巴金的观点又发生了明显的变化。1977年8月的重印后记中,巴金仍然坚持“我的作品已经完成了它们的历史任务,让读者忘记它们,可能更好一些”,而他在同年给法译本撰写的序中仍然强调:“我的书中描写的生活已经不是新中国青年所熟习的了”。但到了1978年11月29日的文字里,他的态度已经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弯,他写道:“这篇序文在这里第一次发表,我想借这个机会纠正自己的一个错误。我前天写成的《爝火集·序》里有这样一段话:‘今天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必须大反封建。去年八月我写了《家》的《重印后记》,我说这部小说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现在我知道我错了。明明到处都有高老太爷的鬼魂出现,我却视而不见,不能不承认自己的无知。’”
为何发生这样的转变?我们必须回到那个历史的现场中去寻找答案。1977年到1978年,“文革”刚结束,正是历史转换的当口,正是“时间开始”的时候,首当其冲的,便是对“文革”的历史评价问题。1970年代前几年的主导话语是“反右”,无论是林彪集团还是“四人帮”,都被看作“修正主义走资派”,是“极右的路线”,但到1978年,尤其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中,将“四人帮”定性为“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的“极左路线”,七八月间《人民日报》的系列文章更直接将“四人帮”定性为“封建主义的阴魂”。而这同一年的11月,巴金正式调整了自己对《家》的判断,他再次将《家》中的“反封建”视作当下紧迫的时代任务了,这其中的历史意味耐人寻味。
巴金不仅是写作序跋,他也通过一次次回顾和重思不断调整自己的创作立场和历史观念,将其与时代的命运紧密相连。从反封建的愤怒呼喊,到反思性的冷静自省,再到对现实社会的警示与镜鉴,《家》的序跋内容记录了一个作家的屈折变化,也记录了一段时代的精神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