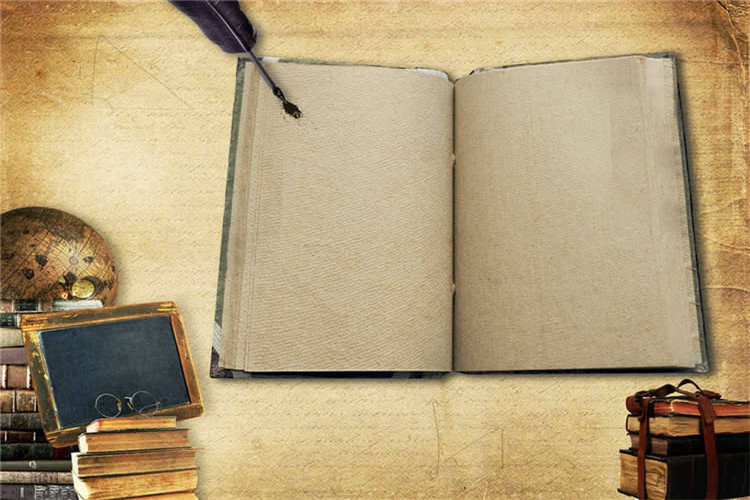文丨暗蓝(书评人、翻译)
对于老练的读者而言,《梅赫川1987》的叙述者“小洋猪”,或许会让人想到君特·格拉斯名作《铁皮鼓》中的小奥斯卡。小奥斯卡为了拒绝成人世界决定不再长高,“保持三岁孩子的状态,却又是个三倍聪明的人”。而小洋猪,“六岁就看清这个邪乎世界的小洋猪”,在1987年因为“白雪球”生了一场病。他这一年的时间得以由自己保全,而非像其他小朋友一样踏入校园,任由自己的时间按部就班地汇入社会时间的洪流。
所以在这一年的东北小镇梅赫川,究竟发生了什么呢?不同于近年来以双雪涛、班宇等人为代表的“(铁锈带)东北文学”,《梅赫川1987》提供的是乡土叙事,这种叙事自然勾连起更广阔的东北文学传统。“河水就这么淌啊淌,是不是流到天边了?人们从来没认真琢磨过,河水最终都流淌到哪里呢?人们不在乎它淌到哪里,一眼望不到的地方,都和我们无关!”如此与鲁迅“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相悖的“梅赫川哲学”,若写得再残酷些,便是萧红在《生死场》中的名句“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
可事物终究不可能一成不变。对于梅赫川而言,1987年是转变之年。然而当转变的真切往事只能由一个并不可靠的叙述者“嗷嗷”道来,读者便需要肩负起韦恩·布思在其代表《小说修辞学》中提出的“双重解码”任务:一方面是解读叙述话语本身,另一方面则是超越叙述者的话语,还原事件原貌或寻找正确的判断。譬如当小说中的关键人物小果义离开后,小洋猪是这样总结的:
就这么多了吧,大伙想不到小果义还给大伙留下了什么。我看着大伙冥思苦想的老脸,忽然就想到了,但是我和谁都不说,这些也许是人家小果义的隐私呢!
小果义留给梅赫川最大的东西,是八十年代的忧愁,人们学会了,扔不掉了,真真地写在脸上了呢。
小果义是小镇的文艺青年,正是他和他的录音机,让梅赫川的人们第一次听到了以《冬天里的一把火》为代表的流行歌曲。而当费翔在1987年的春晚舞台上唱响这首歌,其影响力显然不止于东北小镇梅赫川,而是“火”遍大江南北——也许在无数小镇上,都至少有一个小果义,在对着电视录完这首歌之后,扛着录音机走遍大街小巷。也许他只是为了博得一句“尿性”或其他类似程度与形式的赞赏,也许他真的想要分享自己压抑许久所收获的感动。无论如何,因为小果义,梅赫川终于吹进了全新的风气,人们燃起“勾火”,在雪地上“撒野”,迎来了难忘的“高潮”。
可八十年代终究还是忧愁的,因为沉闷的乡土需要改变,改变需要力量,但流行乐与流浪梦并不提供力量——于是小果义只能黯然出走,只留下人们对忧愁的清晰体察。许诺力量的是气功,于是在梅赫川,小果义掀起的流行文化热很快被小洪伟“大师”的气功热取代——负责任地讲,事情只是在梅赫川这样发生的,倘若它在其他乡其他镇竟然大同小异,那也许只能归结为“如有雷同,实属巧合”。
只是小果义虽然走了,但“一把火”的故事却并未就此结束。小说中一处现实锚点,是写到了1987年的大兴安岭火灾(虽然梅赫川的人们并不知道大兴安岭在哪儿——“在快活镇吗?”),但有关小果义的“一把火”与这场火灾的谣言却不胫而走。在现实中,费翔本人也曾遭遇如此谣言——对于新事物的接纳与追逐的同时,也包含着抵触甚至是恐惧,同样也是八十年代的一种微妙心态。
《梅赫川1987》是一部“可解码”的小说。它所承载的记忆也许唯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表达——固然小说中的插科打诨缺乏节制,但若是不以孩童视角冲淡现实,则转变时期人们所面对的命运,终究残酷得令人难以消受。乡村凋敝的前奏在当时已经隐隐浮现:年轻人或主动离去,或被动逃离;“以前都是死了人才抽地,现在不等死人也可以抽地了”——离去之人的土地被村长非法保有,而村长很快也下了台。只是新当选之人,似乎也并非众望所归……
当然这一切,对于豁达的东北人而言,或许都可以看成“耗子闹腰疼——多大个事儿(肾)”。但这种乐观,终究需要一种开放式的笃定。小说里的小洋猪无比信赖他的文芹妈妈——好比《铁皮鼓》中的小奥斯卡的祖母那庇护了一个家族的四条裙子——每每到情节行到繁难之处,小洋猪便会说“我听文芹妈妈的,她长得好看,她说什么都对”。小说里有一个并不显眼但堪称核心的谜团,是村里人常说“大梅河的水怎么淌,那要听文芹的”。小洋猪不解其意,曾多次询问文芹妈妈,但她只是一笑置之——到小说结尾,当小洋猪最后一次提出这个问题,文芹妈妈最后的回答是“听来的话,不能都当真的”——以“姑且听之”作结,小说的现实性,就这样被轻巧解构。
可这到底只是一种沿袭传统的谦逊姿态。小说所着力构建之物,对于有所用心的读者早已坚如磐石。有关“文芹妈妈”之谜在前文其实已经给出答案:她是当年知青当中的总指导员,带领当地百姓完成了当地河道的整修工作。小说的历史纵深由此得以拓宽:黑土地何以肥沃,也许从来都只与“文芹妈妈”、与年轻人、与渴望生活的人们有关。
也正因如此,人们的盼望才显得真诚,“等到2000年,日子就好啦!”,一种只属于东北乡土的“世纪末华丽”跃然纸上。于是《梅赫川1987》最终是一部关于乡愁的小说,这乡愁并不限于梅赫川或是东北,而是关于那些你我曾经拥有笃定希望的日子——在那些日子里,我们真的相信,“明天会更好”。
(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