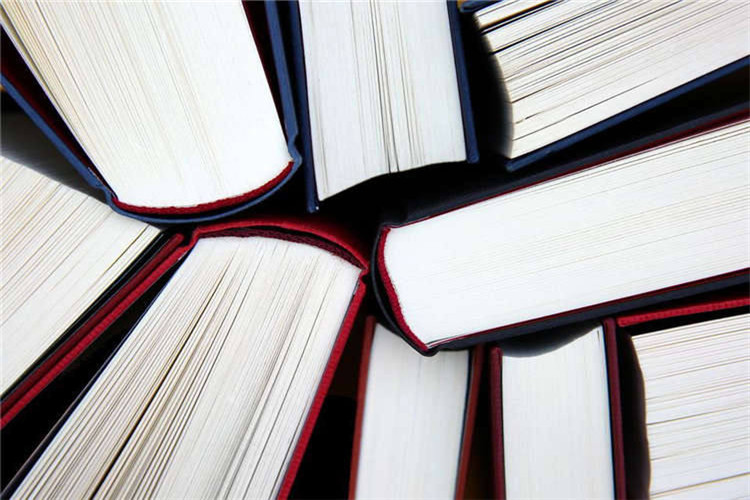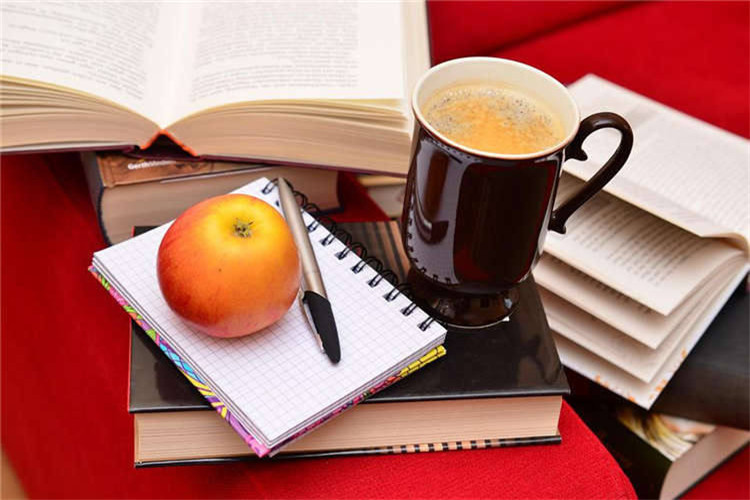对话|刘蟾等谈刘海粟书法人生(上):困境反而愈使他坚韧
史上规模最大的刘海粟书法展“百年吞吐——刘海粟书法大展”从2024年10月下旬亮相上海后,持续成为艺术界热门话题,2025年1月15日是这一大展在刘海粟美术馆展出的最后一天。近日,《澎湃新闻|艺术评论》邀请刘海粟女儿刘蟾,收藏家、刘海粟弟子陈利进行了三人对话,就此次展览的亮点及刘海粟晚年书法何以人书俱老进行了对话。
“我父亲1958年被打成右派,经历了多次中风,十年浩劫被抄家扫地出门,但一直坚持写字看书,他曾和我们说:‘这样的境遇是千年不遇,但这些不会长久的!’困境反而让他更具韧性,他强调书法要有金石味,要求格局要大,到后来他对我的要求就是‘吐故纳新’。”刘蟾说。
晚年刘海粟挥毫
晚年刘海粟与其女儿刘蟾
“他对我的要求就是吐故纳新”
顾村言:“百年吞吐——刘海粟书法大展”即将落幕,这一大展,无论是2023年在中国美术馆,还是在上海刘海粟美术馆,影响比之前我们预想的要大,应当说这还是海老书法作品的魅力所致,这次展览的作品中,具体到您个人,印象深刻的或者说最有意义的有哪几件书法?
刘蟾:说起书法作品,对我来说非常有意义的有几件。我生于1949年,是家中最小的女儿。小时候父亲很忙,时常上海和无锡两地跑,我常常见不到他,家里雇了佣工和保姆。父亲回来,佣工就帮父亲磨墨,偶尔我们会在边上看。有时候他为油画打框,我也手忙脚乱帮一下。父亲很威严,坐在那里不出声,让人害怕。其实他从来没有骂过我们,但就是有一种不怒而威的气场,我们几个孩子从小就怕父亲。
最早我自己偷偷练习书法,我父亲不知道,我在一个小房子里写小字,有一次他进来看我写字,就给我题了一幅字《金石千秋研古、画图四壁得真》,真的是一本正经写的,他和我说:“你要写书法,很好!书法要有金石味。”他因为受康有为先生的影响,后来给我题了这十几个字,说你以这个追求为主打基础,叫我写大字。
顾村言:从吴昌硕先生、康有为先生,尊碑,强调金石气,以书画强其骨力,也是跟当时中国的积贫积弱有关,知识分子要想着把中国人原初的那种精神力发掘出来,所以追求金石味与风骨。
刘蟾:对!他说虽然你是个女孩子,要大气,这就是打基础。不要老是缩缩缩。缩得格局太小,没气魄。你是我刘海粟的女儿,怎么画画格局那么小,要有大气魄!父亲没有手把手教我什么基本功,他就是关键时点拨几句。他的教育风格就是不干涉你,先看你的路子走得怎样。
顾村言:你父亲强调格局、气魄,你看“千秋”两个字,跨越时空的感觉,有史家的意识。
刘蟾:对我有意义的书法,就是从这一幅字开始。当时是“文革”时,我也没有上学,就在家里待着,就自己练字,他看到了,所以说这一幅对我来说特别有意义。
顾村言:你后来就是按着他说的这个路径在学习。
刘蟾:对,我后来也是一门心思的临石门颂等,他很高兴。“文革”之中反而让我画画写字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可能也去考大学、上班了,这反而把我留下来写字了,很有意思的。到后来他对我的要求就是“吐故纳新”,写了一幅字《吐故纳新,蝉蜕龙变》送我,他希望我要变;还有一幅字是《博搜广采冲天劲,勤奋学画持以恒》也是专门写给我的,那时候是1982年,我从香港回来,他说你现在怎么样,我说我去香港生病了,这个腿感染了肿了,一直没作画,我父亲说你还是要多看,多吸收,还要勤奋,你光有天份不行,还得要努力、勤奋,才会使然。
顾村言:他还是鼓励你把书画学好。
刘蟾:对,一直是这么鼓励我。
陈利:这幅《博搜广采冲天劲,勤奋学画持以恒》,气势大,没有规规矩矩,整整齐齐,但字和字的架构,整体是一气呵成,笔画之间都有呼应的。
刘海粟赠刘蟾《博搜广采冲天劲,勤奋学画持以恒》
顾村言:对,开阔,既一气呵成,又苍劲,有一种浩然正气之感。
刘蟾:正气,很大气。他后来教我,你要放开,随意一些。
顾村言:毕竟你当时还是小女生呢。
陈利:刘蟾与她妈妈(夏伊乔)的书法都有一脉相承刘老的风格,她妈妈的字,根本看不出是女书画家写的,也是气势很大,当然她与刘老比起来稍微秀气一点,但不像别的女书画家多写得工整、娟秀,不是这样。她的字也是一样,也是放开的,包括她的画也是受到刘老的影响。
顾村言:这些字从八十年代写下来到现在,四五十年了,几乎是刻在脑子里的。
陈利:所以她的画跟她爸爸不一样,她画的牡丹虽然也是刘家样,但有变化了。第二她的山水也不完全是,有的人就只是父亲画什么样,我就照着这个画,她是刘老一脉,但又不完全一样。
顾村言:因为刘老本身也是这样做的,他学康体,但又变出来、画出来,所以他希望你们也画出来,所以上海美专反而出人才。
陈利:他不拘一格,没有说统统按照我的来学,他说你们愿意学什么学什么。
顾村言:他是很开阔的胸襟在里面。
刘蟾:其实我很喜欢我父亲的字,都是一气呵成的,尽管是斗大的字,但是一鼓作气这么写。
顾村言:他写字的时候,可以感受到能量的充沛,所以说真是“真气流衍”。
刘海粟致李宝森札局部
刘海粟致夏伊乔札局部
陈利:我接下来补充三点。这次展览的刘老书法代表作,其实很多,我就讲三件,第一件是一组,五封给刘蟾母亲夏伊乔的信;第二件是《散氏盘》,是他的篆书当中的代表作,也是书法的代表作之一,第三件是对临陈白阳的草书。
顾村言:确实,代表作其实很多,你说的这三件我也特别喜欢,他临的陈白阳很有意思,虽然说是临,字也差不多大小,但却把自己的胸怀襟次呈现在其中,比原作更加雄浑苍劲,真愈老而愈佳。
陈利:原作与临作展览时放在一起,是一模一样的格局,但两张作品放在一起,陈白阳是不能比的,海老到晚年的时候,笔力雄强,气势苍莽,这是他草书中的一个代表作,《归去来辞》也是代表作,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这件比《归去来辞》更高,感觉是超越前人。
还有一件很多人都没注意到的,是上海美专七十周年写的词,是他自己填的词,字是行书,比较有代表性。
顾村言:是的,其实各有妙处,包括给齐白石纪念馆写的,虽然是行楷间。印象也深,但我最喜欢的还是他的晚年手札。
陈利:信札里面,除了致夏伊乔等家人,还有致李宝森、朱复戡、李骆公、江辛眉等的也好,给朱复戡的好在什么地方,其中所记有在“文革”时的“凛然无畏,刚毅不屈”,这里面都是有精神在里面的,不一样的。如果信札里面选三件是这三组,如果选一组,肯定是家书一组。刘老有很多好作品,包括“海到近处天是岸”,本身也体现了老先生的气魄和胸襟,“海到近处天是岸,山登绝顶我为峰”,到了山顶上,我就是山峰,我比山还高,这样的一种气势。我觉得我主要是学刘老的精神和他的为人,包括我有一些经历跟刘老是相近的;刘老年轻时候的社交,用“社交达人”四字都不能形容,就是“顶流”。他的社交,我觉得后来也继承了他一点,我从年轻时的社交高度、广度,感觉与刘老也是有点像的。现在回过头来看,等到我们能给刘老做一点事的时候才发现,刘老到底原来是做校长的,他就有这个眼光。因为回来想想,认识他的人太多了,他为什么不把别人带在身边?
顾村言:其实无论康有为还是海老,他们看人的眼光都超一流,对一个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他们就能看出来人中龙凤。
刘海粟赠陈利书法《海到近处天是岸,山登绝顶我为峰》
2023年12月,中国美术馆刘海粟书法大展现场,刘蟾(左)与陈利(右)
陈利:我认识海老时刚刚21岁,有这个缘分一直在来往,别人见了一次他可能聊都不聊的。当年我21岁不到,跟朱复戡、施南池,交往都很多,跟海老是比较晚的,因为他那时候整年在贵州、广州写生,1986年以前他全中国到处跑,有时候一年回来不到一两个月的。
外界的压迫来得险恶和凶猛,愈使他坚韧
顾村言:刘老师我们再谈谈你父亲对你的一些影响,你印象里什么时候拿毛笔?
刘蟾:我印象中小时候是学钢琴的,还是傅雷先生介绍的音乐学院老师,我小时候也不懂的,想要出去玩,同学叫我,我坐那里都没心思弹钢琴了,钢琴就放在客厅的阳台间靠外面点,我父亲画画也是在阳台间,有时候他就在这里画,他就不让我出去玩。
顾村言:等于是监督你。
刘蟾:他从来没有怎么教训我,到后来是这样,父亲打成右派后,有一天突然中风了。当时是1958年前后在上海,要大鸣大放,他去发言,拉着傅雷先生一起去,他说现在是大鸣大放,政府需要把什么事搞好,让我们出点意见。动员傅雷也大鸣大放,结果傅雷后来也被打成了右派。当时上海美专和苏州美专、山东大学艺术系调整合并为华东艺专,政府让我父亲继续做校长,后来迁到江苏,他后来说,上海美专应该搬回到上海,这么大的城市没有一个美专不太好,后来就被打成右派,他就中风了。
顾村言:也是精神上打击比较大。
刘蟾:对。中风之后就半身瘫痪了,右手右脚不能动,这个打击很大的,我们还小,当时全靠我妈妈照顾。我父亲一直很坚强的,他说我身体瘫痪,自己精神绝对不能瘫痪,他就说正好在家里躺着,让我母亲把他收藏的绘画正好拿出来研究。
顾村言:当时右手瘫痪,不能动笔了。
刘蟾:不能动笔。那时候我七八岁,记得给他推拿、针灸、吃营养品。中风一两年左右。
陈利:他后来画了一幅,后面题跋有“病臂初平”,就是中风刚刚好。
顾村言:他那时候写字多还是画画多?
刘蟾:写字吧,我还小呢,那时候不敢去打扰他,他书房我一般不进。后来还画油画。
陈利:实际上中风时候已经六十多岁了,那个年代这岁数中风的很多人就没救了,那时候人活到六十岁已经蛮好了,他到六十一二岁还中风了。
顾村言:而且后来还又中风了。
刘蟾:后来是小中风,最厉害的就是1958年那次。
顾村言:其实你刚才说一个人的精神力量是蛮重要的,对身体的保养,精神力量很重要的。海老有一股非常顽强的精神力量,看他的字就能看得出来,他的精神气特别强。傅雷三十多岁写的文章《刘海粟》,其中有:“他在任何恶劣的环境中从不曾有过半些怀疑和踌躇;因了他的弹力,故愈是外界的压迫来得险恶和凶猛,愈使他坚韧。”所以苦难对海老这样的人,反而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
刘蟾:我父亲去世前跟我说的,他的母亲——我的奶奶在他儿时常常跟他讲故事,讲司马迁受刑而撰史记、苏东坡贬黄州而有赤壁赋等,他印象很深,他也常常讲给我们听。
顾村言:因为你们家里本身就是大知识分子家庭,他的曾外祖父洪亮吉就是一代大文人,因敢言获罪,但很快又被召回,嘉庆帝又后悔,觉得这是敢言是为社稷民生,所以这种文人的失意与得意,于他从小经历过。《报任安书》说“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总感觉你父亲这个基因里有洪亮吉敢言的基因。
陈利:真的是这样,用现代科学讲,儿子像娘,儿子的基因都继承母亲的基因,女儿的基因是继承父亲。
顾村言:所以你奶奶对你父亲儿时的教育其实蛮重要的,对一个男孩子来说童年的教育至关重要,所以养成了你父亲这样一种越艰难困苦,斗志越昂扬,越不屈服,他的作品中也一直有一种不屈不挠、昂扬向上的精神。
刘蟾:他在“文革”的时候画梅花,就这个意思的。
陈利:那时候画了很多红梅。
刘蟾:还有葡萄什么的,都是韧性的一种表现。
刘海粟《墨葡萄图》 中国画 1970 年
刘海粟赠刘蟾书法 1982年
顾村言:而且海老对艺术的追求与徐悲鸿不太一样的,他是把中国文人的写意,真正嚼透之后,到欧洲之后有选择性的,在自己文化本体的基础上吸收国外的东西。
刘蟾:他去读书也是有规划的,从古典主义,艺术浪漫主义、印象派、野兽派,他说要研究透,才会出来自己的东西。
陈利:以前有的人说刘海粟到外国人面前去讲中国画,到中国人面前讲西洋画,表面上是贬低,实际上这个话反过来看,反而也证明了刘老这方面的能力:刘老到外国人面前弘扬真正的中国文化,又把西洋真正好的东西引进到中国,把中国好的文化推广到国外去。
刘蟾:就是这回事。
顾村言:而且他吸收的西方艺术,中国人很能心领神会的。
陈利:现在有一条很能历史资料证明了他的正确。在欧洲人还没有给梵高出书的时候,全世界第一本宣传梵高的书其实是刘海粟出的,在欧洲还没有出版前就先出版了,在欧洲人还没有理解接受马蒂斯和梵高的时候,他已经把西方艺术中的马蒂斯和梵高给引进到中国来了。实际上现在也能看到,徐悲鸿的艺术教育理念是崇尚欧洲古典主义艺术包括苏联那一套,刘海粟的艺术理念则是现代性的,与中国文人艺术相通,现代社会和历史已经证明了他的眼光。
顾村言:其实现在整个美术教育体系,比如素描考试,大多是苏式那一套,问题很多,如果延续海老的上海美专教育体系,反而是很健康的,像上海美专那时候的教科书,西方油画、书法篆刻、文史哲都得有。
陈利:上海美专当年连音乐专业都开了,那天有中国音乐学院的博士生导师、歌唱家,带着他的研究生、博士生一起到刘海粟美术馆观展时,我才发现中国最早的音乐教育是在上海美专,上海音乐学院就是在上海美专的基础上,首任校长是上海美专的教师还是学生,音乐,跟艺术有关的,他讲是讲美术专科学校,实际上是中国第一所综合性艺术学校。
刘蟾:我们后来研究,蔡元培先生说的是美育取代宗教,这个“美”是包罗万象的,音乐、雕塑都在“美”里面,不单单是美术。
陈利:最近我讲到,施南池是1920年代上海美专毕业的学生,毕业于上海美专艺术教育系,那时候已经有艺术教育系了,后来施南池是整个上海甚至全国美术方面的领导,包括创办了中国画会,但日本人来了以后,他公职不能再干,他也不能投向日本,所以就辞职不干了,后来又回到上海美专,被刘老请去当教授。
顾村言:我们再回到书画上,刘老师刚才说到,刘老中风一两年之后好了,这也是奇迹。您印象里,随着你年龄的长大,他对书画的追求,印象深的有哪些事?
刘蟾:他恢复健康以后,主要还是出去写生,绘画油画,他为什么很佩服梵高,因为他说那就是中国人写生的笔法,就是线条的构成,所以他很喜欢梵高的。
顾村言:梵高本身也受东方艺术的影响,比如浮世绘。
“这些困境千年不遇,但不会长久的!”
刘蟾:因为他从小是写毛笔的人,所以他写很少用硬笔、钢笔,还是习惯用毛笔字的。到后来也没几年,1957年、1958年年,戴帽了,后来1966年,油画也不能画了,就攻书法了。
顾村言:那时候你们还在老房子,还是搬到瑞金路小房子了?
刘蟾:搬到瑞金路小房子了。1967、1968年,时间不长的。后来我搬回复兴路的时候,住在四楼,下面是工宣队,因为我们又睡书房,又睡卧室,整天看着父亲写米芾,写了一本,他很高兴,就一直写。
顾村言:还有,1966年开始这一段经历,你印象里面对的是怎样的困苦?
刘蟾:刚刚开始的时候红卫兵开始上门抄家,我也跟着其他同学一起去别的地方抄家,等我们抄好了,回来一看发现别的红卫兵在自己家在烧东西,我就不敢进去。
顾村言:你爸爸在家吗?
刘蟾:在,在客厅里。后来我听我妈妈说,他们赶紧叫我哥哥打电话给区委、市委,说这个不能烧,这个是文物。我妈妈也是画画,有临摹的古画什么的,而且我父亲很多写生的稿子,他们找出来就去烧,当时写生稿装在箱子里。
陈利:我看到一个文献记录,一个路过的工人还骂他们红卫兵,说这样烧东西不对,但是也阻拦不了。
刘蟾:他们搬来搬去,有一个路过的人就跟他们说,不要烧,不要烧,红卫兵不管的。我父亲急坏了,赶快让我哥哥把书房最要紧的东西,那时候古画什么的,本来是放在锦江饭店一个地下库的保险箱,后来不能放了,全部要拿回来,结果红卫兵起来了,我父亲急坏了,赶紧把书房的门关上,他们搞到晚上十一点多,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他们说是吃完饭的时候就来了。后来我进去以后,我听到门口这些红卫兵说:“好了好了很晚了,前面还有一家人呢!”就离开了。
陈利:大概任务完成,他们是烧四旧,还不是抄家。
刘蟾:我那时候还小呢,初中生,我看了以后很怕,看着我妈妈打电话,打给上海博物馆的沈之瑜,他是上海美专的学生,他说你们赶快派人把这些古字画保护起来,后来第二天上海中国画院派人来,也来抄家,抄走的东西都统一堆积在龙华的一个仓库。没过多少时间,复旦大学也派人来了。
陈利:这个我插一句,我手里有一封信,这次展览没有展出,是刘老给复旦大学写过信,我原来一直奇怪他为什么给复旦大学写信,他跟复旦大学没关系啊,怎么复旦大学去抄他家什么意思?
刘蟾:复旦大学有一个教授是大右派,他老婆过(世)了,我妈妈也好心,每个星期约他和几个朋友一起来,聚聚吃吃,大家讲讲,还要给这位教授介绍女朋友,后来造反了,他是大右派,他交代到刘海粟家聚会,所以公安就借了复旦大学的人过来。
陈利:这是正式抄家了,前面幸亏给博物馆保护起来了。
刘蟾:抄走了很多书信,我父亲很多朋友的书信成麻袋的拉走了,现在都没有了。以前的信,胡适写的,蔡元培啊,傅雷、徐志摩这些人的信,都没有了。把我们分割了,我父亲在客厅里整天被批斗,我妈妈在睡房里被批斗,我们在地下室交代,晚上在上面睡觉,白天就下来交代。
顾村言:叫你们交代什么呢?
刘蟾:反革命行为,在家里搞什么满革命行为。
顾村言:有没有公开批斗你父亲?
刘海粟黄山写生现场,陪同在侧的刘蟾(右2)与夏伊乔(右1)
刘蟾:没有。他们叫我揭发我父亲,我后来看我父亲睡在那里,让他写。那时候搞了十几天。我妈妈真的吃苦了,小凳子四个腿翻过来,跪在上面,上面还要举着很重的画册,膝盖吃不消,我妈妈就动脑筋,她到卫生间时,正好是抄家把乱七八糟的衣服都堆在浴缸里,她赶快把衣服裹一下膝盖,外面说“上卫生间怎么这么长时间”,这样还好一点,我妈妈受苦了。搞了半天,没什么事,一下子把房间封掉,留了一个客厅给我们住,现在我们吃饭那个方桌子,留了这么一个桌子,四把椅子,阳台钢琴还没有搬走,我们就打地铺,我妈妈,还有我大哥的妈妈,四个人打地铺,刘虬那时候到学校去造反。
陈利:工人是睡地下室,他们有两个工人,一个是帮他专门打油画框的,后面这个男工给他送一点纸、墨,还有一个女的是阿姨,女的阿姨好像不大好是吗?听说她参与揭发。
刘蟾:她也揭发不出什么来。
陈利:拿了你的工资,也不做事,因为工人阶级翻身了嘛。
刘蟾:有一天晚上又有红卫兵来了,戴着红袖章,因为我们前面是个中学,一个很小的中学,他们要钱,抽屉一打开,怎么没有钱啊?我妈妈说,我们没钱,都抄家了,我们就剩桌子了,嘴里在骂,手里拿了一个皮带“啪啪”打椅子,他指着睡在地上的父亲说,这老头子为什么不起来?我们三个人起来了,我爸爸不起来,我妈妈说“他有病,他起不来”。大哥的妈妈坐在那里,抖的椅子直摇,她害怕,这个皮鞭声在她边上打,红卫兵说你怎么了?我妈妈说她年纪大了有病,后来红卫兵骂了一句脏话,说“什么都没有”,就走了。
顾村言:估计也是打秋风的。如果搜到钱,往自己口袋里塞。
刘蟾:后来又来了一大批,说:”这个房子很好的嘛,我们做司令部。”也是中学生。什么封条,他们不怕,全部拆了,说,你们搬到瑞金路去,那是他们以前的司令部,一个资本家的客厅,也是有大门的,还有一个小前门,一个小厅。
顾村言:这挺奇怪的,当时的红卫兵组织分哪个区吗?还是随便一个红卫兵都进来?
陈利:不需要分区,红卫兵组织,随便想来就来,谁想来都可以来。
刘蟾:还有后面的事,搬到瑞金路去,说搬就搬,那个房间一个客厅有这一半大,我们还是打地铺,还是这个椅子这样搬过来。他们那边全栋楼全部打开了,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在,把他们自己老爷子接过来住在那里。
刘蟾:后来我们家的工人挺好的,他就偷偷到原来的书房里拿一点画册、毛笔、墨送到瑞金路的小房子里。还有一个我父亲的女学生是陈钧德的爱人,她给父亲买纸来。
陈利:那个时候她到旧货店去买纸,2分钱一张。
刘蟾:不是旧货店,淮海路的文具店,学生练字的纸,那时候的纸比现在的还好,都是传统手法做的。
顾村言:他那时候坚持写字。
刘蟾:他写字,还看书,他和我们说这样的境遇是千年不遇,以前这都是书上看的历史书才有,造反、焚书……千年不遇,现在我们遇上了,不会长久的。
顾村言:他相信不长久的。
刘蟾:他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他看得很远的,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开始学画画了。我自己看了,就用钢笔拿来画册照着描,我妈妈看了也蛮高兴的,我父亲睡觉了我就去画画。
顾村言:就用他的案台画画。
陈利:台子就一张嘛,他下午要睡午觉。
刘蟾:他起来了,我就赶紧藏起来。
顾村言:后来有没有给他看?
刘蟾:没有,怕!我妈妈就笑了,她说你怎么了,画的东西呢,我说不敢,我妈妈说你要想跟你爸爸一样?我说不,我怕爸爸骂我的,她说坏了就是一张纸嘛,怕什么嘛,人家学生都老远过来请教,后来我就开始,我父亲一看,说,画的小不拉几的,他说要画大的,他也不示范,他从来没有手把手给我画,他说自己画,不行的他给点拨一下,先画松树,用笔大。
陈利:那时候工资是有的,但生活费不发给你们是吧?工资是照发的。
刘蟾:工资是有的,但每个月限20块钱。
陈利:4个人20块,5块钱一个人。
刘蟾:我妈妈就只能保证我父亲有一瓶牛奶。
刘海粟书法大展现场的刘海粟与夏伊乔旧影
1979年,刘海粟与刘蟾在复兴中路旧居
陈利:那时候有一瓶牛奶算奢侈的。
刘蟾:我们平时都是酱菜、青菜吃吃。没有菜就弄点辣酱,辣椒,还不是八宝辣酱,就是辣酱,纯粹的辣椒酱,辣糊糊。后来工宣队来了,把红卫兵赶走了。我们冬天冷了,要衣服,就打电话去上海中国画院,找杨正新去说。
陈利:如果没有杨正新带着红袖章带着你们去拿衣服,自己去拿是拿不到的。
顾村言:这种细节,我们都想像不出。
刘蟾:我们住在四楼,顶楼嘛,法式的房子,整天画画、写字。
顾村言:关于海老书法的变化,其实就是那个时候在酝酿了,当然是有意无意的,从帖学回归金石。
陈利:这方面我补充一句,我听朱复戡先生讲过,虽然刘老师年轻的时候就临过毛公鼎,朱复戡对金石方面有研究,他跟刘老因为几十年的老朋友,他没忌讳,六七十年代时他就跟刘老说你现在再去临临毛公鼎和散氏盘,当时朱跟我讲的,这个录音还有,我有十几盘录音,原件一份给了孙晓云了。朱复戡跟他说,你还是要再去临一临毛公鼎,实际上他原来临过的,因为朱复戡自己也写字,他眼光是有的,所以他跟刘老说,可能刘老就受他的提醒,因为原来临过的,后来空下来又去临散氏盘、毛公鼎。慢慢到七八十年代以后,晚年的字就成熟了。
刘海粟临摹《散氏盘》跋语。1975年
刘蟾:他是反反复复,苏东坡的字也临了很多通,但这里面慢慢吸收不同的变化出来。
顾村言: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对社会的体验、磨难,学养,人格,都会融进笔端的,与年轻时的临写感受肯定不一样的。
陈利:有一句话讲得非常对,我一直是这么认为的,刘老正是因为在1957年反右以后,尤其在文革遇上非常艰难的日子,反而激发了他内心的精神上的东西,他没有地方发泄就去写字,就会画画。
顾村言:而且本身之前是社交顶流,最后应酬也差不多没了——所以反而是幸事,可以回归自己的内心。
陈利:没有人找他了,他也没有太多应酬了,他就沉下心来把字练一下,这个练不是像小学生练字,因为他练字,一是排遣,二是学习,慢慢不知不觉的,因为他的心情、认知、感受,字就形成了,很明显的形成了与前面不一样的书风。
顾村言:就像苏东坡写《寒食帖》,虽然是行书,刚开始还算正襟危坐,心情平和,越到后面,随着心情的变化,写得满纸苍莽悲凉、欲哭无泪的感觉,海老也喜欢《寒食帖》,苏东坡的黄州和海老的“文革”境遇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成就了海老,由于外在的打压和艰难困苦坎坷,让他回归自己的内心反而安静下来。
陈利:他那时候应酬没有了,来往社交也很少了,没有社交了,私下有一两个人偷偷看看他,这个时候他可以彻彻底底静下心来研究书画,他前面的时候社会上的事情很多的,又要出国考察,又要出书,又要管学校,事情很多的,真正沉下心来画画、写字的就两段时间,一段时间是在抗战时期的印尼,还有一段是“文革”中。
刘蟾:印尼的时候也是写苏东坡的字。
陈利:日本人抓他的时候,他都带回来了,一卷一卷都带回来了,这是一段时间。然后就是真正沉潜下来,反而是文革期间。1972年以后,他慢慢社交恢复一点,背景是中国要加入联合国,他大儿子刘虎是联合国高级官员,所以对他开始放松了,那时候海外关系很严重的事,要见海外来的亲戚都要经过居委会、派出所批准的,他见谁都要批准的,后来国务院给他补资助,海外的东西也能寄过来,各种代表来找他,写得来劲了。境遇变好了一点,慢慢心情也好了,但到了1980年代以后他好的手札书法作品写得少了,一是年纪越来越大,二是没有空了,这里请那里请,他哪里有空坐下来给你写一封信花半小时,没时间,后来写的信都很简单,因为那时候没事的时候这个信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顾村言:手札最好的就是1975到1982、1983年这之间,最好的,包括写给家人、李宝森等。
1970年代刘海粟书札局部
1970年代刘海粟书札局部,致李宝森
陈利:刚才讲的书法代表作还有一件,《桂林诗稿》,涂涂改改,写得非常好,在桂林写的没有署名字,他改的过程都看的很清楚,这完全是一个草稿,他在上面改来改去,最后定稿写的毛笔字都是有的,跟《祭侄文稿》一样的。他曾经和我讲书法的要点是十六个字:“大大小小,浓浓淡淡,疏可走马,密不透风”,前面八个字是他独有的。
顾村言:“疏可走马、密不透风”本来是中国书论里讲到的,但“浓浓淡淡”,好象是画家才会这样的,纯粹书法家比较少这样说,黄宾虹他们写字也是浓浓淡淡的,而且,对墨法更讲究。对了,刘老师,你爸爸在书法方面,对你有没有讲过什么要点的话?
刘蟾:没有,他给我解释过书法中的“雨夹雪”,就是浓浓淡淡、疏疏密密。
陈利:他的草书用的笔锋是散的,他写出来的字多飞白,也不能讲完全飞白,因为飞白没有这么多,传统书法中飞白没有这么多,但他的字整个写下来有浓有淡的,有人说,刘老这个字跟康有为学的,但如果去看康有为,康有为有很多枯笔,且枯笔是干巴巴的,按照我个人的看法这不及齐白石的枯笔,齐白石最后的枯笔是像钢刷一样刷下去的,线条、力道都在那里,康有为就是枯,但少润,他没有雪、雨,所以刘老的字,'雨夹雪'的特征,比如枯笔这一部分,另外整体布局上,他有浓淡。
顾村言:燥裂秋风,润含春雨,想到这个“雨夹雪”,我就想到司徒庙汉柏的意象,雨雪下在两千年古汉柏苍老的枝干,苍莽而湿润,有一种汉柏苍浑的线条在里面。
陈利:这个“雨夹雪”将来可以写篇研究文章,刘老的“雨夹雪”体呈现的是他的精神符号。
(未完待续)